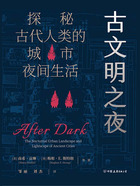
城市环境和行为
夜晚早已被编码到人造的环境中。本书的研究涉及拉普卜特在其大量著作中提出的“环境行为理论”(2006;转引自M.E.Smith 2011)。古人为了从事夜间活动而对城市景观或面貌进行规划,想到这个,我们的视角便能从白天重新定位到黑夜,从光明重新定位到黑暗,空间和建筑布局在内的地貌特征也进入了考量范围之内。一些研究人员把这个学术方向称为空间句法(Baumanova 2020);M.L.史密斯(2016)和达里尔·威尔金森(Daryl Wilkinson)(2019)把这个方向中的一些内容划分为“基础设施”或者“中央发起结构……景观连通性”(M.L.Smith 2016,2)。基础设施在景观中赫然突出,比起单幢住宅,它们会耗费更多的资源、时间和能量。正如人类学家用全球性比较的方式来研究城市化一样,基础设施的研究也可以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借鉴威尔金森(Wilkinson 2019,1216)的分类法,将他所分类的基础设施应用于夜间考古研究,并在夜间城市环境中重新想象它们的形态:①静态型基础设施(如梯田、港口和仓库);②回环型基础设施(如道路、运河、高架渠和下水道);③分界型基础设施(如栅栏、沟渠和畜栏);④信号型基础设施(如灯塔和烽火台)。相比起来,有几类基础设施与夜晚和黑暗更容易自然地产生关联,例如灯塔和烽火台,它们建造的初衷就是抵御黑暗及其他危险。又如栅栏,可以捍卫自己的领地免受偷袭,而偷袭可能发生在夜间,大多会在黑暗的掩护下,或者专挑对方的睡眠时间突然发起。所有城市都有基础设施,所有达到城邦规模的社会也是如此;但是,在没有城市或城邦的情况下,基础设施也可以独立存在(Wilkinson 2019)。
威尔金森(2019,1220-1221)列举了基础设施与建筑的不同之处。基础设施不包括家庭建筑,因为大多数房屋不需要耗费众多的劳力(宫殿除外);基础设施通常是开放式建筑而非封闭式。威尔金森(2019,1222)认为“基础设施通常是能在地形地貌(道路、运河、桥梁、高架渠)上延伸的结构”,并且“基础设施是那些专供容纳事物、资源和废物的建筑环境的一部分”。应当指出的是,如何区分建筑和基础设施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两者在概念上存在重叠是不可避免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有很多关联,还能延伸涉及公共机构与私产拥有者之间的互动(Müller 2015)。例如,古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城内建筑群就是基于民居用于清洁的管道和水井这些基础设施而建造的(Wright and Garrett 2018)。
建筑和基础设施会影响人们在夜间的视野,正如莫妮卡·鲍马诺娃(Monika Baumanova)(2020,137)所说:
类似的观察包括针对古埃及家庭的研究,例如观察人工建造的环境在主人与外来客人的会面交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Spence 2004,2015)。人们会好奇,古代城市的设计师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夜间环境对建筑的影响,因为白天和黑夜里的视域(从同一个位置观看同一个区域的景观)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Kamp and Whittaker 2018)。
古代有围墙的城市不胜枚举,从中东的苏美尔古城,到墨西哥古典玛雅时期的贝坎(Becan)遗址和玛雅潘(Mayapán)遗址、北美中西部的卡霍基亚围栏、津巴布韦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再到法国阿维尼翁(Avignon)等中世纪欧洲城市。城墙阻挡了外来的危险和不速之客,但也可能将危险和不速之客留在城内。围墙限制并圈定了所有权和控制区域的界限(Ekirch 2005;Koslofsky2011)。司各特·哈桑(Scott Hutson)(2016)谈到过“隐私技术”,例如,墙壁可以用于应对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情况,规避“拥挤、失范,(和)健康问题”(51-52)。此外,社区的形成是管控拥挤的一种方式,在居民住宅周围建造围墙能为私人房屋划定边界。城墙也区分了地位,居住在城墙围绕之内的城里人往往比城外居民地位更高。“构筑围墙、建造大门是一种规划行为,带围墙院落的规模、排他性和形制可以彰显规划的级别”(M.E.Smith 2007,24)。
规模不等的围墙,从围绕房屋的到环绕寺庙的,再到城市本身的城墙,它们的大门都受到严密的监控,作为通往安全的门户。大门本身的形式可能与白天和黑夜的相互作用有关。像在古埃及,神庙的塔门象征着地平线,也是Akhet——环境中白天结束夜晚开始的物理分界点(图1-1)(R.Wilkinson 2000,79)。就像地平线是昼夜循环当中的一个重要过渡点,在神圣的建筑中,大门或者入口是两个空间的重要交界所在。跨过门槛即标志着进入了一个神圣领域,将世俗世界抛在神庙的墙壁之外。自愿进入此空间的人会经历各种感官冲击——眼睛可能得适应瞬间从强光到黑暗的巨大落差,暑热会消退,浓烈的熏香弥漫在空气中。
总体来说,针对道路的人类学研究不在少数(Snead et al.2009)。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对美国西南部查科峡谷区(Chaco Canyon)的居民道路网络的研究。罗伯特·S.韦纳(Robert S.Weiner)研究了道路这种基础设施及其在夜间活动中的作用(第9章)。在古典玛雅城市中,若干条道路,或称之为sacbeob[10],将神圣区域和世俗区域连接在一起(Chase and Chase 2001;Keller 2009,2010)。这些道路向上隆起,地表涂有白色的石灰泥,在夜间闪闪发光,方便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享有盛名的神庙通过sacbeob通道相互连接;沿着这些道路,还构筑有花哨的专用宽步道,供部队行军和夜间仪式使用(Ardren 2014)。这些道路也服务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科巴(Cobá)和亚克苏纳(Yaxuna)地区的居民使用的堤道是迄今所见最长的sacbeob通道,这条通道用于货物(例如竞技场红陶瓷[Loya González and Stanton 2013])交换。晚期的古典玛雅人借助这条100千米长的道路将许多居民区串连起来(Hutson et al.2012;Loya González and Stanton 2013),也将沿途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图1-1 表现在埃及卢克索神庙入口塔门上的象形文字Akhet,即“地平线”。照片来源:Meghan E.Strong
研究城市不平等现象的学者对民居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分析(Hutson and Welch 2019;M.E.Smith et al.2019)。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夜晚这一镜头重新审视房屋。贡琳和艾普丽尔·诺威尔(April Nowell)(2018b,11)曾经探索夜间家庭的考古概念(Gonlin 2020,398-399)。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夜晚是私人时间,也是休息时间,这就使房屋及周边环境成为考古学家收集夜间活动证据的理想场所。从城市中心宏伟壮观的宫殿,到分布在城市边缘的肮脏住所,其间的差异为研究提供了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夜晚的社会经济参数进行评估。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也会在每个夜晚出现巨大变化。
房屋遗存也与“投射性身份”相关。M.L.史密斯(2010a,32)曾恰当地指出:“物质文化首先在私人场合被个人精心制作,用来宣誓自我,然后这种自我身份才在公共场合加以投射。”自我身份当中的一部分可能要到晚上才表达得最好。比如,从家中散发出的光亮可能是财富和地位的有力象征,因为屋主显然拥有更多的燃料。无论一个人白天如何与他人往来互动,夜晚住所中透出的亮光是很难隐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