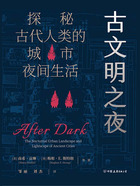
1
城市的夜晚:对夜晚、黑暗及古代城市环境亮度的考古
南希·贡琳
梅根·E.斯特朗
夜晚既卓越又平凡,既神圣又世俗。夜晚自然降临,人类无权阻止它的到来。将夜晚这一维度纳入人类学和考古学分析的范畴后,研究者们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完整的昼夜循环(而不仅仅是“白昼”的生活)在文化内涵和感观上的理解。昼夜循环是地球自转的结果,也是值得探究的文化构成,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为环境决定论[3]的结果(Wright and Garrett 2018,287)。在本书中,学者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将夜晚这个维度纳入古代城市的研究中。通过纵览时空中的不同文化,穿梭于不同的古代世界,一条内容丰富的“夜晚地带”(Reed and Gonlin 2021,7)由此被呈现了出来。众所周知,古代城市年代久远、遗存密集、断代复杂,因此发掘困难(McAtackney and Ryzewski 2017),要研究它们,需要获得诸多资源,以对古代城市的生活信息进行梳理。但是,将夜晚这一维度纳入之后,考古学家们可以获得更加深入和鲜活的理解。一旦进入夜晚的概念框架,学者们便注意到了存在于黄昏和拂晓之间的大量活动、行为和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考古学相关性。
沿着莫妮卡·L.史密斯(Monica L.Smith)(2010a,33)的研究基础,让我们思考时间/时间性的分类,以便将夜晚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影响涵盖其中。莫妮卡在2010年出版的《普通人的史前史》(A Prehistory of Ordinary People)一书给了我们灵感,引领着我们对夜间考古学(Gonlin and Nowell 2018a;Gonlin and Reed 2021)进行深入研究。在重建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两人慎重地考虑了夜晚这一因素:贡琳负责古典玛雅时期(Gonlin and Dixon Hundredmark 2018,2021)、斯特朗负责古埃及时期(2018,2021)。这里,我们在史密斯对人类认知发展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认为,夜晚和黑暗也是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个人和群体征服并塑造着夜晚。夜晚一直影响着人类这个种群,比如在进化过程中我们逐渐能够适应夜晚。灵长类动物的基因深植于我们的睡眠中(Nunn et al.2010),尽管“相对而言,人类睡眠的独特之处在于能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睡得更短促、深沉,并有更多的快速眼动睡眠(REM)(Samson and Nunn 2015)。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工业化国家,人们的睡眠模式与古老的祖先人亚族的睡眠模式迥然不同(Worthman and Melby 2002;Worthman 2008)”(Samson et al.2017,91)。大卫·萨姆森(David Samson)及其同事(2017,97)对当代哈扎狩猎采集者及其睡眠模式进行研究后,报告称,他们发现,影响一个人睡眠时长和质量的因素包括睡眠地点(在帐篷里往往比在帐篷外睡得好)、噪声级别(声音越少睡得越好)。如果将此类模式作为我们采集食物的祖先如何睡眠的代表,当快进到城市化的黎明时期,噪声因素对人类睡眠的干扰就很容易理解了。古代城市的夜晚既像现代城市的,又不太像。夜间的人工照明对人类及其他物种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https://www.darksky.org/)。
同样,黑暗在人类的进化中也发挥了作用,虽然黑暗并不等同于夜晚,但两者都常常被用作多种事物的隐喻,如越轨、功能障碍,还有死亡。然而,有时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黑暗会被刻意地寻求、期待或依赖,例如睡眠、仪式、巫术(Coltman and Pohl 2021)、天文学、庆典及摄影。黑暗的程度在人类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觅食群体(与朱洪西人[4]的炉边谈话研究[Wiessner 2014]),到哈扎人的依披密(epeme)舞蹈研究(Marlowe 2010),再到后工业时代的夜班工作者。人类无法创造自然的夜晚,但他们可以制造黑暗,或者寻找光线不受欢迎或不必要的所在,例如洞穴的内部、封闭的庙宇。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物种能像人类这样处理夜晚和黑暗。借助人类的创造力,我们改变了城市的夜间环境,本书展示的正是这一行为在考古记录中的诸多具体表现。证据一直在场,但是考古学家并非总能从这一角度切入,对夜晚进行具体探究,在考古学中,这相对而言是个全新的领域(Gonlin and Nowell 2018a;Gonlin and Reed 2021),即便在普通社会学范畴内也是如此(Palmer 2000;Ekirch 2005;Galinier et al.2010;Koslofsky 2011;Edensor 2017;Dunn and Edensor 2021)。在本书中,我们研究夜晚,并将此研究作为具有解释功能的镜头,以期回答关于文化演变,尤其是城市转型等更为宏大的问题。黎明或日出也需要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解决一些问题,正如艾娅泽克赛尔·柯吉提·仁(Iyaxel Cojti Ren)(2020)所研究的黎明传统在古代卡奇克尔玛雅政体(Kaqchikel Maya polity)中的重要性那样。
自古以来便众所周知,过去的人们不一定像我们现代人一样,把一天划分为标准的24个小时,也不考虑季节性,还对白天、夜晚的吉时赋予称呼(例如Laurence 2007;Martínez 2012)。雷·劳伦斯(Ray Laurence,2007,154-166)就“空间的时间逻辑”进行写作时,描述了公元1世纪时,庞贝的古罗马人每天分时段地使用城市的不同空间——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白昼和夜晚决定了罗马人的时间概念:尽管白天和夜晚各分为12个小时,每个小时的时长却因季节的不同而有显著不同(Laurence 2007,156)。例如,“在夏至,白天要比冬至多出6小时”。研究那些有明确空间位置的活动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季节进行的,可以让我们对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层面的活动有更深入的了解。尽管房子内部没有明确地划分男女空间,但男人和女人使用频繁的房屋的部分往往是不同的。对于精英来说,家庭空间存在按时间划分的情况,男性主导着一天的开始和结束,女性则负责一天里的中间时段(Laurence 2007,162)。如果一个人是庞贝社会的男性精英分子,“这种规则模式意味着精英们每天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比如,早餐后,他们会奔赴公共集会场所开始自己的工作(Laurence 2007,163)。男性精英对城市的程序化使用与其余人口的无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受雇佣者的工作多种多样,且以任务为导向,与现代概念中的8小时工作制形成鲜明的对比。把对夜晚的研究放进这更广阔框架的同时,我们也鼓励那些有兴趣将日常实践扩展到全天时间的研究。
对城市环境的研究历史悠久(Pirenne[1925]1969;Childe 1950;Adams 1960;M.L.Smith 2010b;Creekmore and Fisher 2014;Hutson 2016)。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想讨论的是:城市意味着什么;城市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城市由什么构成以及该如何定义城市(Wirth 1940)。尽管新近的定义不再仅关注人口数量(Alt and Pauketat 2019)。不管怎样,只要听到“城市”一词,立刻勾连起无数感官体验。在人类熙熙攘攘的喧嚣里,城市生活的场景、声音和气味主宰了人们的感官。至关重要的是,大多数城市环境早在电气发明之前就被人类占据、使用,于是这就又增加了一层额外的感官体验:黑暗。黑暗能唤醒属于它的知觉,再与城市环境相结合,便创造出了独特的夜间景观,即城市夜景。考虑到以上方面,我们着手描绘太阳落山后、明亮的电灯普及之前,生活在古代城市中的情景。
城市化进程已在全球不同的时间、地域及环境中铺展开来。无数理论关注着这一过程,从经典著作(Childe 1950;Adams 1960)到新近研究(Bietak et al.2010;Harmanşah 2013;Cowgill 2015;Moeller 2016;M.E.Smith 2019;M.L.Smith 2019)。然而,夜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尚未被常态化地纳入到研究视野当中。不过,安第斯考古学家阿列克谢·弗拉尼奇(Alexei Vranich)和斯科特·C.史密斯(Scott C.Smith)(2018,134)的一项研究表示:“蒂亚瓦纳科[5]最初的选址,之所以能持续地作为农牧民互通的场所,可以归因到它基于夜空观察的生命周期”。在其他领域,当考察建筑环境和天空景观时,月亮的作用正是中美洲研究的一个主题(Šprajc 2016)。
大量的考古证据显示,古人既能做到基本应对黑暗的城市环境,还能在这种环境中繁衍生存。在(重新)审视具有夜晚特征的物质文化时,考古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古代城市环境,同时推进黑暗和夜间考古学,还有古代照明学,即对古代人工照明的研究。聚焦于夜间环境的多感官体验,以及城市居民中不同人群在夜间所经历的刺激,其过程也有助于感官考古学(例如Skeates and Day 2019)的发展。
继迈克尔·E.史密斯(2007,2011,169,171)之后,考古学中的中层理论[6]对于填补数据与宏大理论之间的鸿沟至关重要。史密斯(Smith 2011,173)在他研究历史的经验方法中专注于“城市的布局或形式、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活的社会动态”。考古学家可以思考城市环境如何在夜间的黑暗中得到使用,建筑环境的方方面面如何与黑暗和夜晚产生关系。
我们可能会关注生态位构建理论(Laland and O'Brien 2010;O'Brien and Laland 2012)以帮助理解城市现象,一种由人类专门创造的情境,也是我们擅长的情境。早在我们的祖先建造能遮风挡雨的建筑时,我们的生物模式就开始受到影响,比如睡眠(Samson et al.2017)。城市景观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由文化构建的生态位,它仅由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物种创造,人类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舍弃它,因为万千城市仍然存在于世间(M.L.Smith 2019,262)。今天,全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比生活在城外的人还多的局面。城市环境的开发创造吸引了更多的人,城市居民人口日益增长。历史上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受到推拉因素[7]的影响(Anthony 1990;Gonlin and Landau 2021),那些因素要么吸引人们进入城市,要么将人们排斥出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用夜间角度来重新审视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等城市环境。在这种复合视角上,阿莫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的作品具有伟大的启发性。研究城市环境的考古学家们采用了他的建筑学视角,且受益匪浅(例如M.E.Smith 2007)。这让我们能关注到考古学家们希望研究的多个方面,同时又不失整体格局。拉普卜特(Rapoport 1990,15)的分析包含4个变量:“空间、时间、意义和交流”。在这里,我们引用拉普卜特的一段话,其中就将夜晚作为时间变量的一重维度(添加下划线处):
正是基于拉普卜特(1990,13)的研究,我们得以利用时间元素把建筑环境与夜晚联系起来:“把环境定义为由固定景观元素[8](建筑物、地面、墙壁等)、半固定景观元素(各种“陈设”、内部和外部空间),以及非固定景观元素(人及其活动、举止行为)三部分构成,是有裨益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属于“固定景观元素”,从考古学角度讲,它们是最坚固持久的。拉普卜特(1990,13)告诫说:
除去个例(Sheets 2006;G.R.Storey 2018),极少有重要的半固定景观能历经时间而不湮灭,于是只剩下固定景观元素能成为考古学家解码古代生活的依据。
建筑和基础设施的确与夜间活动直接相关。例如,站岗和进行交易一类的经济活动(如墨西卡[或阿兹特克]社会的pochteca,或者说商人[Nichols 2013,56]通过大门、道路、记账,还有仓库等场景与夜晚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样,埃及祭司们的夜空观测成果对皇家墓葬群的设计来说至关重要)(Magli 2013)。夜晚可以被用来突显社会的不平等:一些人耽于夜晚带来的休闲和松弛;而另有一些人,例如宫殿和仆人的住所呈现出忙碌的景象,奴仆们在黄昏时需要伺候、照料那些心血来潮、放纵不羁的客人。精英们则在夜晚肆无忌惮地挥霍燃料和食物,通宵达旦地聚会,丝毫不用担心需要早起趁着日光照料家务。废弃堆积和照明相关的文物证明了这些活动的存在,也丰富了建筑和基础设施的遗迹。
现代世界,城市中的人类被自然且稳定的人造光所包围。人造光模糊了白天和黑夜。于是,昼与夜,以及与昼夜相关的活动的差异在我们当代人的生活中变得不再明显。今天,自然光照的变化规则已被取代,我们改造自然生物的节奏已经到了危及自身和其他物种的地步(Chepesiuk 2009;Naiman 2014)。如果要书写一本关于现代城市夜晚的书,显然已经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天黑之后”[9]了,因为,灯光永不熄灭。这也是巴黎作为最早拥抱瓦斯路灯的欧洲城市之一,被称为La Ville Lumière(光之城)的原因。白天和黑夜的融合也渗透到我们对过去城市的审视习惯中。即使100年前,无论是低密度还是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也与我们现代的城市体验显著不同。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审视不断变化的城市夜景,关注夜晚和黑暗的考古活动,这能让我们借助想象拼凑暗夜里的城市面貌——那里的城市居民曾在其中设法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当然还包括与活动相关的物品和意义(拉普卜特所说的“非固定景观”元素)。古人如何在城市里体验黑暗?与此息息相关的考古材料往往以文物、地貌、建筑、基础设施和遗址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