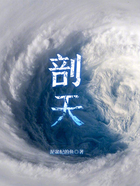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25章 有槽
疑心一旦生出,便再也止不住,连风也卷不走半分。最终它是被任天富响亮的脚步声和失了稳重的惊叫打断的。
“波哥!12点的卫星数据来了!”
任天富扒在门框上冲陈相喊,两手湿漉漉的,还在滴水,显然他这厕所上了不止一次。
两人一同回到值班室,除赵栋梁以外,所有人都围在陈波的座位前,连椅子都被拉好了。
陈相仔细查看那张云图,但关注点不在台风的位置上,而在湛江北部上空的水汽分布上。水汽图的对比度并不如可见光和红外图那样高,纯黑底图上总是弥散着丝丝缕缕的灰色痕迹,那是波长7微米左右的电磁波穿透整层大气时,在路径上测得的水蒸气含量的总和。
他所关注的地方,在这个时刻还没有被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到,所以在红外图象上显示为黑色,代表该地区上空无明显云层。而水汽图上,当地被灰白色占据,与西北方的大团白色连成片。
湛江及北部地区的水汽在12点的时候就已经不少了,来源为西北方向的暖湿气团,这和天气图对不上。在天气图上,这里盘踞着一个局地高压系统,大气低层持续吹东北风,而东北方向很干,干冷暖的空气平流过来,应该把当地的水汽驱散才对。
天气形势和卫星图像对不上,二者之间必有一个是错的。如果放在一年以前或者更早的时候,陈相一定会本能地认为是天气图在出错。因为在计算机仍未普及的年代,天气图由人工手绘。那时,气象台里最重要的岗位不是预报员,而是填图员。
填图员坐在与报务室一墙之隔的填图室内,从一个互通的小窗口接来报务员递来的报文,把它们填在写在底图上。底图上绘有各城市、观测站的位置,以及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等等地理标志,本就令人眼花缭乱,标注好数据后,更是复杂得像捅了蚂蚁窝。
而填图员则要操着蓝色的蘸水笔,一气呵成地在上面按规则画出光滑的线。这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十分繁重。报文每三个小时接收一次,一次填图过程就需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填图员们需要像打仗一样,不敢有丝毫放松,否则一旦填错、绘错、绘慢,就会给后续的预报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不出错。在那时,绘图快出错少的填图员会被授予“优秀填图员”的称号。这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至高荣誉,其余的,则只能在腰酸背疼和眼睛干涩中挣扎几年,带着一手老茧默默退场。
1995年起,名为MICAPS的气象信息综合处理系统彻底解救他们。新型电报机自动译码,地面、高空和卫星数据全部被集成在一起,利用网络统一分发给各单位。填图员的业务归并在预报员的工作中,从繁重到连部队转业人员都吃不消,变得轻松到只需要轻轻点击一下鼠标。在算法的加持下,无论多复杂的场景,计算机都能够瞬间把图绘制出来,并且总能完美无瑕。
所以,在计算机统治一切的当下,天气图和卫星图像这两份产品都值得信赖。陈相无法凭借主观经验轻易判断,于是把求救的眼光投向任天富,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用有限的脑力和脆弱的肉身,审判踔绝的机器之力。
自从台风登陆这一事实被认可之后,任天富那副自信果敢的神态完全消去了。他眼神慌张,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焦虑,声音依然急促洪亮但明显是在强撑。陈相把各个气压层上有疑点的天气图铺满界面,用鼠标在关注的地方画圈圈,引导任天富在其上寻找错误。
这是一种高级版的“我们来找茬”游戏,既考验眼力又考验脑力,从线条密匝得要放大才能看清的图像上,找到几条连错的线或者一个不合群的点,在没有参考答案的前提下。谁也想不到,在填图员彻底消失的半年后,有两个人开始不自量力地体验他们的过往。
凌晨1点10分,雨已落下。时缓时急的雨滴砸在腐朽的门板上,发出脆响,听起来像是头脑中的零件正在断裂。围在电脑前的所有人都屏气凝神,连一向话痨的张勇都安静得像入定的老和尚。
赵栋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在陈相的隔壁,面对聚精会神的人们的背影,哗啦啦翻书,口中念念有词,念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话,像夏日夜晚的蚊虫,吵得人心神不宁。
不知过去多久,那只不安分的蚊子终于觅到满意的食物,安静下来。他放下书,站起身,也凑到电脑前,抿着嘴唇,像在酝酿着什么话。下一秒,任天富惊叫出声:“这条线不对!”
任天富手指500hPa图上,广西贵州湖南的交界处,画了一个圈,“这个地方,看起来像均压场,但其实有个冷中心没给圈出来。588线既可以从这地方北边一条线贯穿到南亚去,也可以走海口站从南边绕。在第二种情况下,这里应该有个又小又弱的冷涡,是深厚系统,低空肯定有槽!”
算法永不出错的高光一旦被抹除,千疮百孔便尽数显现,像被食肉动物破解保护色的斑马群,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遁形。任天富和陈相两人开始操着各色铅笔,在屏幕上涂抹,把有问题的天气图尽数修正。这个过程十分简单顺畅,连张勇都能提出一两个有见地的想法。不稍一会儿,极限平铺在窗口上的6张天气图全部修改完毕。
浅浅的笔痕悬在光滑通透的屏幕面板上,危若朝露,好像马上就能被空气里弥散的水汽润开、洗掉。摆脱既往认知的桎梏之后,面对眼前这台解放无数枯槁灵魂的机器,陈相第一次感到烦心,烦心精心设计的算法也终有失误;烦心无论再用力,笔痕也无法穿透面板与底图融为一体。面板和其下整齐排列的液晶分子相距不足毫米,微不足道却无法跨越,就像横在人类智慧和机器智能之间的那道沟渠。
时间指向凌晨1点30分,名为Sally的恶魔如期把这栋立在山头、四周毫无遮挡的下楼吞入口中,细细咀嚼。风噪贯穿一切,厮磨在耳边,令人心颤,但陈相的心境却格外明晰。任天富正拿着修正后的天气图,向张援朝汇报。模式也已被重新驱动上,使用最新接收的卫星数据和重新插值突出冷涡形态的观测资料。
如果一切顺利,那么20分钟后,陈相便可以得到一份完整的模式结果,在其上,台风的登陆路径与现实相差不大,强降水中心会出现在瑞云湖附近。接着,在风暴潮席卷一切之前,他有机会用这份结果说服张援朝炸堤,救下数万人的性命。除了张瑾玥的。
他并不知晓张瑾玥现在身处何处。按照过往轮回的记忆,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从裁缝铺返回,打着伞。可那把孱弱的绸布伞并不能为她带来任何庇护,灾难面前的惊心也将让温暖羊水里的东西失了安稳。如此这般,承载着两条生命的脆弱之躯迟早要倒在疾风冷雨里。
她也许会坚持、会呼救,但却无法逆转注定死亡的未来。因为按照第一次轮回的经历,要不了多久,他便可以接到人民医院的电话。
在风雨来临前见到张瑾玥并把她送到人民医院,是救下她的唯一方式。可在当下的情境下,这显然不可能实现。因此,在等待模式运行的20分钟内,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要把凌晨一点多才能传送过来的卫星数据记下,这样,在下一次轮回中,便可以在晚间11点前让模式正确地运转起来。最多晚间12点,他就可以安排好台里,搭上陈德球的顺风车,把张瑾玥接到人民医院,默默等待到凌晨2点,彻底结束这荒谬的一切。
完成这样的设想并非一件容易事。卫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是0.1度。要想描述台风对当地的影响,模式模拟的域至少要设置为20度×20度,即便使用嵌套,最内层的域也要覆盖住整个雷州半岛,至少有2度×2度。意味着他需要在剩下的10多分钟内,精准记下400个浮点数。这着实是一种挑战。
在结束被试卷支配的五年后,他重拾起学生时代的疯狂。满屏数字摆在面前,目光贴在上面,像蠕虫一样从左上角吃到右下角,咽进肚子里,刻在脑子里。
聚精会神之下,感官变得混乱,风雨的呜咽变得模糊,苔藓的潮土味和遥飘来的鱼汤香气却格外清晰,仿佛置身于二横巷老房子内,在一个阴郁的下午,坐在卧室里,大敞着窗,厨房里咕咕嘟嘟冒着热气,张瑾玥马上就要推门而入,喊他吃饭。
目光扫到屏幕右下角时,他被推门声打断,有人喊他的名字,粗厚的嗓音,以焦急的语气。
“陈波!模式结果拷贝好给我,水文站要据此计算洪水路径。”
张援朝话音刚落下,模式结果输出。在标有0701 01:00 BJT的图像里,白色年轮的中心如愿出现在霞山区海岸,但降水中心错误地出现在遂溪县,北桥河上游。一瞬间,心中的安然与笃定被击破。
通常,这是一份优秀的预报结果,因为遂溪县和瑞云湖相距不足10公里,不比模式的水平空间分辨率大多少。但在眼下的情况下,却再糟糕不过。
霞山区在赤坎河南边,赤坎区在赤坎河北边,遂溪县在赤坎区西北方。预报结果把强降雨中心错放在遂溪县,水文队就会把防洪的焦点放在北桥河沿岸和整个赤坎区,不可能按陈相的心愿把赤坎河北岸的堤坝炸掉,不炸南岸的就不错了。这样一来,最好的情况是霞山区北部的居民被捎带着撤离,最差的情况依然是赤坎河以南汪洋一片。
即便按好的方向想,考虑到风暴潮潮锋会出现在霞山区,把海边的居民撤离,也完全来不及了。已经凌晨1点50分了,就算是神仙也不能在短短20分钟内把上万人从凉席上、毛巾被下抽出,撵他们上高楼上高山。
无力回天的绝望下,陈相离开坐位,默默注视张援朝迅速浏览一遍结果后,把一张已经贴好标签的光盘塞进光驱。张援朝不光拷贝了结果,还拷贝了模式的参数和初始场,也许是要拿去水文站那边跑耦合模型,预报海浪。
在这个年代,市话的带宽是128kbps,即便是专线,也最多提高三五倍,把张援朝的数据传送到几公里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至少要十几分钟。也许,在另外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也有一群人正在度过无眠之夜。他们焦急地等待数据,利落地把它们塞进计算机里,在算法推演的未来中,只看到一片死亡。
“叮铃铃铃铃……”
红木桌上,大红色话机如期响起铃声。响到第5下时,任天富刚好湿着全身冲进来,把电话接起,边听边把脸转向陈相的方位,面色惊恐。
任天富的那张脸,淌着水渍,被忽明忽暗的灯光映得汪亮。陈相听到有人叫喊他的名字,却动弹不了,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捉到半空中,从这个世界中抽离,成为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
他看到任天富的嘴一张一合,接着所有人都把惊愕的目光投向他。赵栋梁把手中那本无比珍爱的书扔到地上,跑到话机旁,抢走任天富手中的话筒,很快又放下,冲出值班室,连门都不关。
雨丝和水汽不断入侵室内,把一切都变得氤氲。眼前的光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变得没有边界,像无限膨胀的白色气球,挤在脸上,挤得人窒息。
2020年,陈相升为首席预报员的第一年。
俗话说,人的一生,就是和社会磨合的过程,磨掉毛刺,磨掉棱角,才不至于伤到自己,才能从郁郁不得志中摆脱,逐渐发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陈相的磨合过程很成功,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依靠出色的预报水平和在气象服务类业务中的突出贡献,顺利评上中级职称,并被授予首席预报员称号。而他那位可有可无的父亲则更加厉害,调动到省台后,尽心尽力卷了五年,被光速提拔为台长。可谓是双喜临门。
在消息放出之后,每个认识陈相的人,都疯狂恭祝他,好像他的未来注定飞黄腾达。但陈相非常清楚,那些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的人,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看似恭喜他,实则是在恭喜赵栋梁。毕竟,台长是实权实职,而首席,一个地级市气象台的首席,只是一个荣誉称号而已,象征性的涨几百块钱工资,业务上说话的分量重一些,连一虚职都算不上。
不过他还是开心的。赵栋梁的工资涨幅可观,能让名义上的三口之家全然摆脱拮据的状态。这样一来,陈相自己工资里补贴家用的部分便可以被攒下来,尽早攒出10万元。10万,是陈相这个岗位的离职违约金,只要付了,就能干干净净离开,再无人能阻挠半分,无论于公还是于私。
早在年少时,陈相就替赵栋梁担起了畜妻之责。如果早年间赵栋梁能以工作忙为缘由逃避家庭责任,那么现在,他再无借口。
台长的工作主要是上传下达,组织协调,维护和农业、应急和水利部门的良好关系,除汛期以外的日子里,根本没有不着家的理由。更何况,赵栋梁50多岁一把年纪了,这个时候被提拔肯定是因为人事变动青黄不接。最多一两年,他就会被调往办公室或人事这种纯行政部门,无论职级多高,都不会忙到脚打后脑勺。
如果到那个时候,赵栋梁继续对张瑾玥不管不顾不着家,那么陈相打算揪起他的衣领,忍着嫌恶直视那张冰山老脸,质问他当初是不是为了房子才和张瑾玥结婚,是不是把妻子当服务员,把孩子当冤家?
想到这里,陈相不禁心中暗爽。碍于维持生活的温饱,碍于父权的威严和张瑾玥的慈心,他从未表露过自己的这番揣测。他已花费小半生的时间按捺自己的疑虑,如果赵栋梁连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那么他定将顺势撕破脸面。
至于眼下这份做得还算顺利的工作,打一开始,就不是他想要的,未来也不可能是。羡煞旁人的首席名头,对于他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首席预报员将成为台内天气预报的决策人,在和上级部门会商时的话语权重也很大,发表任何意见都要深思熟虑,否则就有牵动到他人财产和性命的可能。
他向来不是心怀大爱之人,不会听到救护车警铃后虔诚祈祷,更不会对素未谋面之人产生没来由的牵挂。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坚信身处混沌世界,没有谁能干涉到谁的因果,但首席的名头硬是让他成为耗散系统中的一个吸引子,和百万人的生命轨迹产生密切联系。
他不是担不起这个压力,也不是不享受指点江山带来的满足感。他只想要生活得更加轻松自由,更加有滋味一些。他擅长做这一行没错,但把一个热爱奔跑的孩子束缚在轮椅上,是对灵魂的残忍剥夺。
所以,在还能勉强被称为孩子的年纪,他打算抛却一切放手一搏。几年的大胆追逐,成则给予张瑾玥红红火火的生活,败则治愈自己因心智早熟而创伤不堪的童年。横竖不亏。
他在心中规划好一切,连台里的“后事”都安排好了。把科研项目和预报业务都委托给林姐,再把小谢教出来辅佐她。高梵头脑灵光细心认真也是干预报的料,但和自己一样心思不在这行上,就让她去接任天富的班,放气球。
至于任天富,他打算走之前向领导美言几句,把任天富调到预报岗上来。那位总是耷拉着眼角神情畏缩的老大哥,基础特别扎实,是个深藏不漏的人才。在被罗诚汉折磨的那几个月里,他总是拿着罗诚汉给出的变态习题,偷摸向任天富求救,没有一道是任天富答不上来的。这让陈相不禁怀疑,这种惊世骇俗的人才放了一辈子气球,铁定是得罪了哪位小心眼的领导。
预报是一门科学,一个技术活,只依靠经验和脑力。而这两者和所谓的综合素质、办事能力等等抽象的东西不一样,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预报得准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不会有任何内耗和恶行竞争,谁也抢不走谁的果实。哪怕是任天富这种木讷老实的人,也定能轻松崭露头角。任天富本不该被埋没如此之久。
在被悉心培养三年,成为精密仪器上的核心零件后立刻离开,这看起来确实有些不忠和负义。但俗话说得好,不是离了谁地球就不转了。付出事先约定的代价,安排好具体的工作,让一切错位的人和事都回归正轨,没有谁会因此变得不幸。
想到这里,陈相的心情变得格外轻松。早秋的风被清晨的阳光煨出一丝暖意,落在身上温和又干爽。太阳东升,叫醒一切,玻璃窗随风振动的咯噔声和遥远的鸟鸣混合在一起,像一首调子轻快的圆舞曲,让人想要踮起脚尖跟随节奏转圈。
无数次,他在夜班的末尾,在疲惫的尽头,来到这个僻静角落思考人生,却从未有心欣赏这幅活力之景。
早上八点半,陈相吃掉食堂第一笼出锅的小笼包,一边用纸巾擦嘴角的辣椒油,一边往乘车点走。
卸掉心中的包袱之后,原本黯淡的一切都被重涂上色彩,一些生活中的细小之景一下子变得格外有趣。食堂的小笼包他吃了三年,今天第一次发现窗口上除了摆着醋壶以外,还立着一瓶自制辣椒油。蘸辣椒油是二横巷包子铺的专属吃法,没想到也能传到这里。
路过观测场时,正值每天早八点气球施放工作收尾。二次测风雷达的矩形枝桠下,坐落着一间简易集装箱房,任天富夹着一本厚厚的册子从中走出,身后跟着高梵。这是高梵第一次放气球,显得十分兴奋,一蹦一跳的,老远看见陈相,用力挥手。
陈相并没有给出什么反应,只装作没看见。高梵自进到台里的第一天起,就对他有着独一份的热情。今天给零食明天给水果,一有机会就要凑上来聊几句,比对她的同级同学谢家铮都要热情。不知道的,还以为陈相才和她是老熟人呢。
对于高梵的做法,陈相从没往积极的一面想过。如果换作他人,可能会顺其自然开启一段朦胧的感情之旅,但陈相从未怀有类似的期望,只维持普通同事的关系,不冷不淡,不亏不欠,甚至有时还会心生反感。
赵栋梁的存在,仿佛在他额头上戳了一个台长儿子的印章,别人老远看到他,都立刻戴上名为势力的面具,让他无法分清哪些人本就真诚,而哪些人在刻意演绎。所以,在那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血液之间,他更看好不善言辞的小谢,即便他清楚小谢的资质远不如高梵。
陈相不曾想到,终有一日,自己也会戴着扭曲的眼镜看人。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最为安全和省力的做法。
任天富和高梵立在观测场附近的林荫地下,热烈讨论着。陈相走近时,高梵立刻跳到他面前,神情激动。
“任老师说,那个气球,升到3万米高空的时候,在爆炸之前,能膨胀到100倍的大小。”高梵指着天,语气感慨:“100倍诶!它在我手里的时候都有1米见方了,100倍就是100米,太大了吧!真的假的?”
高梵这番言论让陈相哭笑不得。眼前这姑娘,真是应了她的名字,一身多余的艺术细胞,放个气球不关注回传的数据,反而在意它在天上是什么样子。
“你任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没人比他更了解气球。”陈相连忙把话题转到专业上,“地面气压和高空气压你都测到了,气球胚子的延展性,你往里面冲了多少氦气,你也都知道。不信的话自己算一算就是了。”
“我当然知道怎么计算。”高梵仰着头,眼里满是神往,“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心情。几万米的高空,下面是粉蓝色的曙光,上面是淡绿色的气辉层,一个柔软的白色气球悬浮在两层之间,像一朵离群的云彩,不断生长和蒸腾。这多震撼啊。”
一时间,陈相不知道怎样接话。这种过于浓重的感性和浪漫,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的。不过他并不讨厌这些。能在苟延残喘的生活里,保持对美好事物的感知,这样的人,大多拥有一颗柔软的心。就像张瑾玥那样。
任天富显然很崩溃,他让高梵回到集装箱房里监视数据回传的情况,然后拉着陈相到僻静的角落,压低声音讲话,一脸无可奈何。
“她是被招到预报岗上的吧,在我这边轮岗体验一下就会跟着你和林芳了吧。我真招架不住她。”
“她胜任不了?”陈相心里十分认同任天富的感受,但还是这么问了。
“不是不胜任。她手眼利索能干肯吃苦,记性顶格好,说让背手册一会儿就背完了。”任天富焦虑地望着集装箱的方向,抓耳挠腮,“但她太跳脱了。我让她至少每隔10分钟看一眼回传数据的情况,检查到异常值,及时汇报,看情况申请补测。结果她问我,不能写个程序自动检查吗?”
任天富露出一副不可理喻的神情,“机器把事都做了,还要人干什么?机器能有人细致?她思想有问题。骨子里依赖机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蒙蔽双眼,看不到故障。咱们这里现在是基准站了,观测出问题那可是不小的事故。”
面对任天富的吐槽,陈相没做声。他的想法和高梵反而是一样的,但在三年前,被现实毒打后,他再也没向任何人表露过。
“你愿不愿意去预报岗?”陈相问。看到任天富露出一脸错愕的神情时,又补充道:“我也觉得她不靠谱,想让她接你的班,把你调去预报岗。”
任天富的脸色没变,一点都不像陈相想象得那样惊喜,这让陈相有些意外。到预报岗后,职级工资不变,再多拿一份绩效工资,完全能把任天富的生活质量提高一截。
一线核心业务多,素材也多,做做科研,发发论文,以任天富的能力,绝对能带着正研高工的名头退休,退休工资比他现在在职还要高。辛苦一辈子,好歹安享个晚年。
这种好事落到谁头上都要乐开花,任天富是在纠结什么?
正当陈相打算把满腹疑惑吐出时,任天富的脸色变了。从惊讶,到转瞬一逝的神往,再到无法掩饰的失落。眼里是不甘和委屈,但脸上写得却是认命和自甘堕落,像棕榈树光洁又沧桑的树干一样,令人矛盾。
“那我的观测业务谁来接手,高梵吗?她做不了这个的。”
这下轮到陈相惊讶了。任天富直接错开话题,问出了一个本不该他操心的问题。
陈相想不通,就算任天富再木讷,也能意识到,正在提出这个绝好机会的人,是在预报业务上拥有极大话语权的首席,更是省台台长的儿子。
虽然陈相从未想要和赵栋梁在工作上有任何交集,更不可能为任何事情去求赵栋梁什么,但外人并不清楚二人之间的关系。
在外人眼里,相比于“我是首席”,“台长是我爸”显然更能给陈相的提议背书。面对唾手可得的机会,任天富不紧紧抓住,反而顾左右而言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需要谁来做。”陈相忍着疑虑推进话题,“放气球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事,迟早也要全面自动化,就像被淘汰的人工观测那样。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硕大的观测场甚至不需要任何人来维护,机器自查报警后,会自动把厂家叫过来维修。”
“至于高梵,你不用担心她。她的心不在这里,迟早要走的。”陈相说完这句话后,在心里补上一句:和我一样。
太阳已高照,逐渐增大的天顶角让光线褪去3000K色温特有的柔和,艳白的光把一切景物的轮廓变得锐利。任天富站在棕榈树枝叶的阴影下,始终沉默,直到嗡嗡的引擎声从半山腰的发车点传来。
“算了。”任天富以两个字终结漫长的思想斗争,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巨大的包袱,“没用的。”
“你不怕未来有一天被机器淘汰掉吗,那样的话,就只能去后勤管理矿泉水和打印纸了。”陈相不假思索地追问。在他看来,一个技术人员去做是个人都能做的工作,是一种残忍的流放。
“我已经被淘汰了。”任天富一脸释然地轻摇下头,接着捂起肚子慢慢走向主楼,只留陈相一人愣在原地。
“哧——”
客车气垫门的放气声传到耳畔,那是发车的最后信号,但陈相并没有追赶班车的冲动。他死死盯着任天富的背影,任由蓝白涂装的大客车消失在自己的余光里。
任天富在人前永远是一幅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姿态,像被狠狠打压过的、没自信的孩子。但刚才,他却展现出陈相从未见过的笃定,像是以非神之身上达天意,一眼洞穿自己的未来。
陈相看不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