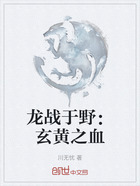
第2章 崖山初探,儒馆问道
鸡鸣三遍,天光微亮。卜子敖辞别了泪眼婆娑的母亲和面色复杂的父亲。卜田耕终究是放心不下,将家里仅有的一小块腊肉用油纸包好,塞进儿子简陋的行囊。
“到了城里,莫要惹事,好好跟先生学本事。”卜田耕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声音有些沙哑,“若是不成……就回来,家里还有几亩薄田。”
卜子敖重重点头,眼眶泛红:“爹,娘,你们放心,我一定学成归来!”
他背起行囊,最后望了一眼生养他的小山村,毅然转身,朝着山外的世界走去。昨夜那位自称孔门弟子的白衣青年,名唤言述,已约定在崖山城东门等他。
山路崎岖,晨雾弥漫。卜子敖脚下生风,心中既有对未知的忐忑,更有对未来的憧憬。走了约莫两个时辰,山路渐宽,人烟也逐渐多了起来。偶尔能看到三三两两面带菜色的流民,拖家带口,眼神麻木地朝着远方迁徙。也有几队行色匆匆的商旅,护卫们警惕地打量着四周,马蹄扬起一路尘土。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这是乱世的注脚。
临近中午,一座巍峨的城池轮廓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青灰色的城墙高耸,如同匍匐的巨兽,城门洞开,人流车马川流不息。这便是崖山城。
比起偏僻的山村,崖山城无疑是繁华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旗幡招展,叫卖声、车马声、谈笑声不绝于耳。行人摩肩接踵,既有绫罗绸缎的富商贵人,也有粗布麻衣的平民百姓,更有一些穿着奇特、气息迥异之人,让卜子敖大开眼界。
他看到城门口的卫兵,身着统一制式的皮甲,手持长戈,目光锐利,站姿笔挺,隐隐散发出一种冰冷肃杀的气息。他们的腰间似乎佩戴着某种金属符牌,偶尔闪过一丝微光,让周围试图插队或喧哗的人不自觉地收敛行为。卜子徒然想起老者所言,这莫非就是法家道统的力量体现?以规则约束秩序?
他又看到街边角落,一个头戴方巾、身穿道袍的老者正在摆摊,面前铺着一张画满符文的黄布,上面摆放着各种符箓、丹药。不时有人上前询问,老者捻须微笑,口中念念有词,指尖偶尔跳动着细微的电光。这大概就是父亲口中“骗人的把戏”,那位游方道士的同类?可卜子敖如今却不敢再轻易否定,这或许便是道家符箓之术的冰山一角。
卜子敖按捺住好奇心,径直来到东门。远远便看见城门一侧的柳树下,言述一袭白衣,手持竹简,正安静地站立着,仿佛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
“言先生!”卜子敖快步上前,恭敬行礼。
言述转过身,温和一笑:“子敖来了,一路可还顺利?”
“顺利,多谢先生等候。”
“无需多礼。”言述点点头,“儒学馆就在城西,我们这便过去吧。”
言述在前引路,卜子敖紧随其后。穿过繁华的市集,走过几条幽静的巷弄,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片占地颇广的建筑群。没有高墙大院,只有几排整齐的青砖瓦房,门口一块朴素的木匾,上书“崖山儒学馆”五个古朴的大字。
与城中的喧嚣不同,这里异常安静。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书卷气,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涤荡着人的心灵,让人不自觉地放轻脚步,收敛心神。卜子敖甚至感觉胸口的胎记微微发热,似乎对这里的气息有所感应。
“这里便是学馆了。”言述介绍道,“馆主乃是鲁国大儒颜路的弟子,在此传授儒家经典,教化一方。”
进入学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的庭院,院中栽种着几棵松柏,更添肃穆之气。几名穿着同样布衣的学童正在洒扫庭院,见到言述,纷纷停下手中活计,躬身行礼:“言师兄。”
言述点头示意,带着卜子敖穿过庭院,来到一间名为“明德堂”的讲堂。堂内已有数十名学童盘膝而坐,年龄大多与卜子敖相仿,也有稍长一些的。他们面前都摆放着矮几和笔墨竹简,正襟危坐,神情专注。
一位须发皆白、面容清癯的老者端坐于讲台之上,手持戒尺,正在讲解《论语》。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
言述带着卜子敖在后排角落找了个空位坐下,示意他先旁听。
老者讲的是“克己复礼为仁”。卜子敖听得云里雾里,许多字词他根本不认得,更别说理解其中深意。但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努力去感受那种氛围,那种蕴含在字句之间的“道理”。他发现,当老者讲解到关键之处,或者有学童朗声背诵经典时,空气中似乎有微弱的光华流转,而他胸口的胎记,也随之产生若有若无的温热感。
“这便是‘文气’吗?”卜子敖心中暗忖,“通过学习经典,明悟道理,就能凝聚这种力量?”
一堂课毕,老者目光扫过众人,在卜子敖身上稍作停留,微微颔首,并未多言,起身离去。
言述这才对卜子敖道:“方才讲课的,便是馆主颜师。儒家修行,首重‘明理’与‘修身’。读圣贤之书,明晓天地君亲师之序,懂得仁、义、礼、智、信之德,此为‘明理’。依理而行,克制私欲,规范言行,培养‘浩然之气’,此为‘修身’。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卜子敖听得似懂非懂,只觉得这条路与他想象中的“神通”相去甚远,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修为。
“那我……该从何学起?”卜子敖问道,他连字都认不全。
言述笑道:“莫急。儒家之道,有教无类。你先从识字、习礼开始。馆中每日上午听讲,下午习字、诵读。晚间则需静思己过,反省一日言行。此乃‘养气’之基。”
他顿了顿,看向卜子敖:“子敖,儒家修行,非一朝一夕之功,需持之以恒,更需坚守本心。你可有此决心?”
卜子敖想起父亲的期望,想起言述先生的风采,想起那惊鸿一瞥的“言出法随”,用力点头:“先生放心,弟子定当勤勉刻苦,绝不辜负先生期望!”
言述欣慰地点头:“好。我先带你去安顿住处,领取学馆衣物和基础书简。”
接下来的日子,卜子敖便在崖山儒学馆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被安排在学馆后院的一间简陋的学舍,与另外三名家境贫寒的学童同住。每日天不亮便起床,洒扫、晨读,然后去明德堂听颜师或言述等师兄讲课。下午则在书房练习写字,一笔一划,力求工整。最初的日子异常艰难,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如同天书,繁琐的礼节让他手足无措。同舍的学童,有的因为他出身农家而隐隐带着轻视,也有的因为他识字缓慢而暗自嘲笑。
卜子敖咬紧牙关,将所有委屈和困难都默默承受。他白天刻苦学习,晚上别人歇息了,他还在油灯下辨认字形,背诵《千字文》。他牢记言述先生的话,每日睡前静坐反思,虽然不懂得如何“养气”,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心绪变得比以前平静了许多,看问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冲动。
而最让他感到奇异的是,每当他全神贯注地诵读儒家经典,尤其是那些关于“仁”、“正”的篇章时,胸口的双龙胎记便会散发出持续的温热感,仿佛在与书中的文字产生共鸣。这股暖流流遍四肢百骸,让他精神一振,学习的效率也似乎提高了不少。
一个月后,卜子敖已经能勉强认全《千字文》,也能磕磕绊绊地背诵一些《论语》的片段。虽然在众多学童中仍属末流,但他的进步速度,连言述都感到有些惊讶。
这一日,言述将卜子敖叫到庭院的松树下。
“子敖,你入学一月,进步尚可。”言述温和道,“但儒家修行,不只是读书识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今日,我便教你儒家入门的根本心法——‘存思守正’。”
卜子敖精神一振,恭敬聆听。
“所谓‘存思’,便是存想圣贤教诲,思索义理。所谓‘守正’,便是恪守中正平和之心,抵御外邪侵扰。”言述缓缓道,“你且盘膝坐下,闭上双眼,心中默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感受此句中的浩然之气。”
卜子敖依言坐下,闭目凝神,开始在心中反复默念那句他刚刚学会不久的话。起初心猿意马,杂念纷飞,但渐渐地,随着一遍遍的默念,言述讲解过的含义在心中流淌,他仿佛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光明,在驱散内心的蒙昧。
就在此时,他胸口的胎记猛地一烫!一股远比平时诵读时强烈得多的暖流骤然涌出,瞬间贯通全身!他只觉得眼前似乎不再是黑暗,而是出现了一片朦胧的玄黄二色气流,如同他梦中所见的天地漩涡的缩影,而那句“大学之道”的念头,仿佛化作了一颗种子,落入了这片玄黄气流之中,开始汲取着某种奇异的能量,缓缓生根发芽……
言述站在一旁,看着卜子敖周身隐隐散发出的微弱白光,以及他眉宇间那股不同寻常的专注与宁静,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这孩子……果然不一般。他的道种,似乎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更加深邃和奇特。
崖山城外,风起云涌。儒学馆内,道种初萌。卜子敖的修行之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