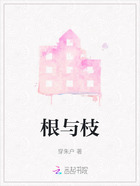
第2章 成分与流离
1922年深秋的张家,丘陵间蒸腾着新谷的香气。张有田蹲在自家祠堂门槛上抽旱烟,听着里屋传来婴儿啼哭。接生婆将襁褓递来时,檐角铜铃正被北风吹得叮当响:“老刘就叫守业吧,盼着他能守住咱张家的基业。”
这话说得祠堂梁柱间的燕子都扑棱翅膀。张家祖上确曾显赫,光绪年间在十里八乡有六间榨油坊,门前拴马石能排半里地。可到有田这辈,就剩三十亩薄田和半山坡的樟树林。守业出生那年,正逢军阀混战,村头老樟树都被流弹削去半边树冠。
一、油坊灯火
守业七岁就跟着三哥守财学榨油。张家油坊虽已破败,但那些包浆发亮的木榨机仍在诉说往日辉煌。寒冬腊月里,他踮脚给炒菜籽的灶膛添柴,看三哥抡着撞锤“嘿哟”一声撞向木楔,金黄的油线便顺着竹槽流进陶瓮。
“手脚麻利些!”守财总拿烟杆敲打石槽。这个三哥继承了张家祖传的暴脾气,有次因伙计偷喝香油,抡起撞锤把人追出二里地。守业最怕他发火时鼓起的太阳穴,像要爆开的山核桃。
1938年鬼子打来那日,油坊梁柱间还挂着“童叟无欺”的匾额。马蹄声惊飞檐下麻雀时,守业正把新榨的茶油装坛。三哥抄起撞锤要拼命,被父亲死死按在榨槽下。等马蹄声远去,油坊只剩满地碎陶片,香油渗进土地,引来成群的蚂蚁。
二、红纸灯笼
冬至那夜特别冷,守业摸黑去后山给父亲烧纸。火苗舔舐纸钱时,他听见三哥在坟茔间嘶吼:“当年护着油坊挨鬼子打,如今倒成罪过了!”月光照着新立的木牌,上面“张有田”三个字还渗着松脂。
1951年惊蛰,村支书带着红纸灯笼来保媒。二十九岁的守业穿着补丁褂子,看王家人把两袋糙米摞在柴房门口。“入赘去还能带十斤粮票。”母亲说话时不敢看他眼睛。那盏写着“王”字的灯笼在夜风里晃,映得墙角蛛网忽明忽暗。
三、唐家屋檐
王家媳妇是生产队记分员,总嫌守业“不像庄稼人”——他晒完谷子要筛三遍,挑水定要打满八分桶,连劈柴都要按纹理码齐。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秋收后,当守业把交公粮的麻袋缝成一般大小时,媳妇踹翻了粮斗:“装什么精细人!你现在姓王!”
这段姻缘维持了四年零三个月。离婚那日,守业背着蓝布包袱走过村口,老樟树的叶子落在他肩头。包袱里裹着母亲留下的铜顶针,还有半块刻着张字的榨油木楔。
1957年谷雨,唐家寡妇托人来说亲。守业蹲在借住的牛棚里搓草绳,听媒婆说得口沫横飞:“唐家媳妇贤惠,就是命硬克夫...”他抬头望见梁上燕子衔泥,忽然想起油坊梁间的旧燕窝。
新婚夜,唐氏在桐油灯下补衣裳。守业注意到她将线头都咬得齐齐整整,针脚密得能藏住星光。“柜子第三格...”女人怯生生提醒。打开却是按大小摞好的粗瓷碗,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工农识字课本》。
四、梅岭晨雾
1960年闹饥荒,守业带着妻儿上岭去挖观音土。三岁的大儿子饿得直啃他衣领,唐氏默默摘下陪嫁的银簪子。守业夺过簪子时,发现簪头刻着细密的樟树纹——竟与张家祖传的油坊徽记一模一样。
“当年我爹在你们油坊当过学徒。”唐氏在月光下坦白。守业摸着那些凹凸的纹路,忽然明白妻子为何总把他的旧衫补得不着痕迹。那夜他们分食最后半块麸饼,饼渣落在《识字课本》上,像撒了把星星。
1978年冬,村支书送来褪色的土地证。守业摸着“张守业”三个字,老茧刮得纸面沙沙响。退还的祖产里有两亩樟树林,他坚持要捐给村小学做课桌。锯木头那日,他反复抚摸年轮,仿佛看见七岁那年飞溅的油花。
五、樟木清香
2021年清明,我扶着爷爷站在老樟树下。八旬老人执意要自己拄拐,中山装口袋里露出半截木尺——那是用祖传榨油楔改的,刻度已被岁月磨淡。
“当年这树淌出的油,能照见人影哩。”爷爷捡起片樟树叶,叶脉在他掌心舒展成七十年前的油线。风掠过山坡,新栽的樟树苗沙沙作响,恍惚又是那个深秋的清晨,七岁孩童踮脚往灶膛添柴,油坊梁间的燕子正啄食遗落的菜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