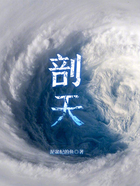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36章 启程(100%)
“6月的最后一天,又是我来送气球的日子。那天我的车出了点毛病,一路上坏好几次,好不容易凑活到地方,你们台里那个大山坡实在是上不上去。
我在山脚下修车,修好时恰好遇见陈波还有那蓝衬衫小伙子,两人抱了好几个气球下来,还说其中一个要给我。
那天我都快哭出来了,贵虾第二天一早就手术,当晚给不了他就再也没机会了。我是打好了主意,如果诺言没兑现,就再偷一个去。
陈波求我载他们到瑞云湖还有几个地方兜一圈,还说要刮台风发大水把西二路最繁华的那条巷子给淹了,给我听得腿直哆嗦。可人家有恩于我,我再害怕也强撑着跟他们干了。
我们把一车氢气卸在原地,留下四瓶载着走,到四个地方悄摸把气球全放完后,我在人民医院下车找贵虾,车留给他们了,他们还要返回台里。
贵虾下床小跑着扑到我怀里,我专门拿着鼓风机求护士长让我用下插头充气球,她看贵虾可怜就答应了,安排我到三楼里专门给大夫休息的办公室里充。
那一晚,贵虾特别高兴,笑得小脸红扑扑的,像没生病一样。玩够了,就睡在我怀里,睡得特别死,连后半夜鸣警报都听不到。
那天和陈波说得一样,确实发水了,有人拿大喇叭喊我们不要出门,没过多久水就来了,把街上都淹了,但淹得不深。”
陈德球说到这里,骤然停顿了。他脸上的喜色已全部褪去,换做一副哀伤的样子,那种陈相见识过的,淤着散不去的哀伤。
“后来呢?”陈相忍不住催促。陈德球口述的这段故事到此为止都是完美的,是陈相已只晓的。他好奇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那个把一切美好都极限反转为悲剧的结局。
“后来啊,后来的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到底算不算是个幸事。
水退下去的那一天,忽然有一伙儿人找到我,找到医院来,说要我配合调查。
他们有的穿制服,有的是领导模样,都细细地问我那晚发生的事,一连问了三遍问到我不耐烦。
我没偷气球,甚至还帮气象台一个大忙,载着他们去放气球,这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我一五一十回答他们的问题,发现他们最关注的是我的车的行驶轨迹和那些氢气的去向。
我哪知道这些啊,那天晚上我在人民医院下车,车借给陈波,陈波没还给我。
我让他们去找陈波,他们告诉我陈波死了。陈波死了,跟我的车一起沉在南桥河里。卸在气象台门口的那堆氢气也都不知去向,他们找了一整天都只找到一半,有几瓶还是泄露过、炸过的,要么焦黑,要么压力表没读数。
我一听就急了,陈波死得蹊跷,我的车也没了。那是运输队的车,是我租来的,把我卖了都赔不起。贵虾的手术因为发大水没做成,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的车又没了没法赚钱,万一贵虾就这么去了,我都没钱葬他。
我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他们赔我的车。他们只把我拉起来,说一些‘肯定给我解决‘这种模棱两可的话。那个时候,我都想死了得了。
但好在,你们这台里啊,都是好人。有个叫张援朝的跑到医院里来见我,给我赔不是,还说要给我赔车,但因为他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求我等等。
他给我两个选择,一个是一个月后赔我钱让我赔给运输队;一个是和运输队的领导打声招呼,不追究我那车,但我也没法再回去拉货,他可以给我在气象台谋个差事,让我去饭堂做饭。
我一合计,一个月后才能有车那这一个月都没活儿干,我捅这么大篓子运输队也不一定要我。所以干脆选择了第二个,去饭堂做饭。做饭好啊,稳定又轻松,你们这还是个国家单位,说出去也好听,还能给贵虾带好吃的。
第二天我就去做饭了,饭堂里就一个大师傅,刚退休,剩下的帮工细胳膊细腿的都抡不动大勺,我就成为主心骨。
我干得可卖力了,备菜、炒菜、打饭、打扫卫生,没一样是我不干的。饭堂有个小三轮是专门用来买菜的,我也老开出去,和开大货一样风光。
有一天,你们台里几个小年轻求我载一车东西到二横巷,说要去看陈波的媳妇和儿子。我一听就答应了,我也想去看看,陈波是我恩人,是我刚认的弟弟,他家里人我肯定也要去照顾照顾。
在路上,他们告诉我,陈波当班期间擅自离岗并且造成巨大安全隐患,本来被定性为渎职罪,但又因为他说准了刮台风和发大水,救了几万人的命,所以功过相抵不追究他的责任。
他们还说那天陈波车返回气象台后本来呆得好好的,忽然又开着已经熄火过的车沿南桥河一路北上东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发大水不久后,车彻底报废,连人带车都滑河里去了。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二横巷,你妈做了一大锅杂鱼汤招待我们。那个时候她已经出月子,但还不知道你爸没了。他们骗你妈说你爸到野外做什么高大上的观测,没信号联系不上。
那是我闻过的最香的鱼汤,汤还没盛出来,我的口水就先出来了。我狼吞虎咽吃完一碗后,缠着她细细地问她怎么做,跟她吹牛说我是台里的大厨学会后可以让全台人都吃上这么好的汤。
那天,她特别高兴,不光教我做汤,还叫我做凉粉草,说陈波也爱吃这个。走之前,她还让我抱了你,你那个时候特别胖,胳膊像藕节一样,不哭不闹,和贵虾小时候一样。”
说到这里时,窗外橙红色的晚霞已被粉紫色取代,最后一丝阳光消失在地平线上,激出的余晖带出几颗黯淡的星。陈德球止住话,木然望着陈相面前的碗。碗里的杂鱼汤已经凉了,凉粉草也开始融化塌陷。两人就这么久久对望着,目光都比初升的星星还要黯淡。
陈相并不明白陈德球的那句开头语“到底算不算是个幸事”是如何总结出的。26年前的那个雨夜,陈波的行为与自己经历过的几乎完全一致,连淹死在南桥河这一点也不例外。一个救下几万生命的功劳,轻易就被一辆卡车和几个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氢气瓶抵消了,这怎么可能算作幸事?
更重要的是,陈德球的后半段故事里,一直缺少一个主角——他的贵虾。他始终刻意回避他最爱的贵虾,只在故事的末尾堪堪提起一嘴。这个被刻意忽略的主角一定是陈德球生命里最大的伤痛,不愿再提及的伤痛。
神经母细胞瘤即便放到当代,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病症,贵虾一定没能熬过去。不论陈波还是贵虾,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这无尽的沉默是被陈德球率先打破的,他抬手擦了一下未被沾湿的眼角,再放下手时,重新换回一副笑脸,“不说这些伤心事了,你的汤凉了,我赶紧再给你热热。一会儿我孩子该来接我下班了,说要为我庆祝退休。”
陈相没有把碗递给陈德球伸来的手,只惊喜地问:“贵虾还活着?”
陈德球笑着,但却摇了摇头,“贵虾死了,连手术都没等到就死了。他是睡觉的时候走的,走得很安稳,眼睛弯弯的像在笑。他去天上追气球了。”
“那你刚才说你孩子……”
陈相的话将将问出一半,眼前的景象就给出了答案。有一个穿白色碎花连衣裙的姑娘蹦蹦跳跳到陈德球身后,一把揽住陈德球的肩。这姑娘陈相再熟悉不过了,这是高梵。
“爸!我们今天去吃涮羊肉吧,是你最爱吃的,给你庆祝!”高梵兴高采烈地摇晃陈德球的肩膀,摇了一阵才发现坐在对面的人是陈相。
她扫了一眼陈相,换做一幅生气脸问陈德球,“你跟我们陈首席说什么伤心事了,让他脸色那么难看。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能这样呢?”
陈德球讨好地冲高梵笑了笑,然后对陈相解释,“这是我女儿。贵虾走后第五年,有媒人给我介绍一个寡妇,说她克夫,刚把自己丈夫克死,正好我克妻,我俩组合在一起以毒攻毒,命气相衡,对双方都好,也省得祸害别人。”
“克什么克的,什么年代了还迷信这个。”高梵敲打陈德球的肩膀,嘟着嘴说,“那神婆还说我活不过3岁呢,可我今年都23了!”
陈德球讪笑着叹出一口气,“是是是,你说得对,神婆的话确实不能信。神婆说我不会再害人,可我还是把你妈给克死了。”
“真扫兴。”陈德球提起旧事,显然让高梵很不高兴,她数落陈德球一番后,立刻把话题岔开,岔到陈相身上,“首席恭喜你,终于离职成功了。太羡慕你了,什么时候我也能走啊。”
陈德球听后也提起一幅架子,“哎呦,搞得好像是谁不支持你走一样。我说我给你交违约金,你偏不让。你爸我可是想全力支持你的,可你不给我机会啊。”
高梵白了陈德球一眼,把脸仰向一边,“就你兜里的那几个子儿,留着自己养老吧。省得回头你看病没钱,我还得上街上卖艺挣去。”
两人一言一语的打趣中,天已经完全黑了。渐起的晚风丝毫不闷热,透过噼啪作响的塑料门帘,把珊瑚藤的香气送进来,送到早已沉醉在此番温馨之景的陈相的鼻腔里,没有像往常那样打断他的一切思绪,让他忍不住深呼吸。
眼前这对父女的关系是羡煞旁人的,但陈相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像是馥郁的花蕊里藏着一根刺,把一切美好都变得不完美。
高梵显然是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的,她也肯定有无数次机会摆脱,在更年轻的时候,拥有更多可能的时候。也许,眼前的这位慈父,曾经也如赵栋梁一样武断专制,也因一己私欲扼杀过孩子的一切,直到最近才幡然醒悟,不再阻挠,甚至开始赎罪。和赵栋梁一样。
高梵似是看透了陈相的心思,抱胸撅嘴问陈德球,“你快跟我们首席说说,我是怎么选到这个专业的。”
陈德球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她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让她选了个能进到气象台里工作的专业。我没文化什么都不懂,就只知道你们单位里的人好,肯定不会欺负我姑娘。我耽误我姑娘了。”
“这份责任我跟我爸一人一半。”高梵冲陈相解释,神情格外认真,“我大学期间只知道傻呵呵地上课考试,快毕业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那时我刚刚对金钱有概念,知道自己家里是个什么情况,我没有试错的机会,只好先俯就于此。”
高梵说着把自己都逗乐了,笑着补充,“不过现在好了,我用一年时间尝试从零开始做自媒体,已经在靠视频播放激励攒违约金了。用不了多久,我也能跟你一样,离开这里,去追只属于自己的梦。”
高梵惯常的明媚笑脸此时在陈相眼中格外明亮,让他记起自己对着银行卡余额计算日期的日日夜夜,也记起无数次立在走廊尽头独自内耗时吹在脸上的冷风,更记起3天前的那个雨夜,她举着亮晶晶的手册立在自己面前的模样。
于是他开始摘掉眼前扭曲的眼镜重新审视有关这位美丽姑娘的一切,猛然发现她散发着治愈一切的美好。彻底斩断和赵栋梁之间的关系后,他才有机会发现,他的生活并不是处处蒙灰。
他收起先前努力消化信息时的木然与迷茫,笃定地望着高梵问,“你还差多少钱?”
高梵眼珠翻了翻,眼睛眨了眨,思考几秒后回答,“大概,5万。”
“这钱我给你出,现在就走吧。”陈相说完,迎着高梵逐渐瞪大的眼睛又补充一句,“我们一起。”
剩下的一切都顺理成章,被冷落的打印纸防潮袋最终还是用上了。当缺失四分之一圆满的上弦月用温柔的光为地上的景物勾勒出阴影时,气象台的下山路上,出现两个并排缓步的身影。一个怀抱毫不拥挤的纸箱,另一个肩扛满满登登的塑料袋。
迎面的夜空十分深邃,星星比月亮还要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