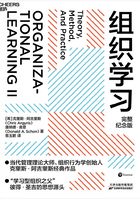
个体学习不等于组织学习
我们可以先假定,鉴于组织是个体的集合,因此当个体成员或一部分个体成员进行学习时,就是组织在学习。但我们略作思考就会认识到,个体学习与组织学习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在许多情况下,个体成员所掌握的知识并不能转化为组织的特定思考或行动,此时组织知道的信息少于其成员。例如,社会服务机构常常会用“单亲”、“受虐待儿童”和“不健全家庭”来划分其服务对象,但机构工作者却知道这并不能抓住服务对象的关键特征。在某些情况下,组织似乎不能学会全部成员所掌握的知识。当错误变得“太严重而不堪承认”时,组织可能会强行推进全部成员都认为鲁莽的行动。相反,在某些情况下,组织所掌握的知识似乎又远多于其个体成员。例如,即便军队或电话公司的个体成员远不算出色,其组织结构中已确立的机制、流程与记忆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让组织取得卓越绩效。
上述思考表明,我们应该从包含个体思考和行动的“组织环境”的角度来探索组织学习。一直以来,组织都被视为人际互动的行为环境、行使权力的场所、约束个体行为的制度化激励机制,或个体参与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8)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或许可以从上述一个或多个角度出发,来阐述要从个体的思考和行动中孕育组织学习,需要具备哪些组织环境条件。可是,这种方法仍未解决如何把个体现象与组织现象联系起来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把组织学习视为最高管理者的特权,他“为”整个组织学习。然而,在复杂的大型组织中,最高管理者时常抱怨无法把学到的经验传授给下属。最高管理者的更替也可能会很频繁,但其他的组织部分却往往稳定不变。当组织学习发生时,可能与最高管理者没什么关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看作“为”所属组织学习的行动者。例如,中层员工群体可能会通过相互交流找到解决生产难题或提高产品质量的方法。然而,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所孕育出的学习结果不一定能融入整个组织。即使这个群体的学习结果已广为传播,也仍可能不会被纳入影响组织政策、程序、实践的讨论或审议过程中。
因此,我们仍旧面临这个关键问题:个体的思考或行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组织的思考或行动?
学习本身(思考、认知或记忆)就是一种行动,并且检验组织学习发生与否的关键,是可观察的新行动是否真正地取得了成效,因此从逻辑上看,组织行动先于组织学习。那么,除非我们明白采取行动对组织而言意味着什么,否则就难以理解学习对组织的意义。
每当个体成员采取行动时,都意味着组织在“行动”吗?若是如此,那么组织与个体的集合似乎就没有多大区别了。然而很明显,某些个体的集合可以构成组织,另一些却不行。此外,即使某些个体的集合显然构成了组织,这些个体也可以做许多不属于组织行动的事情,如吃饭、睡觉、散步、与朋友闲聊等。
组织必定是个体的集合,但又不只是个体的集合。组织行动不能化约为个体行动,也不能化约为组织内所有个体的行动,但没有个体行动就没有组织行动。那么,“个体的集合构成了采取行动的组织”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有意义呢?
以自发抗议大学助学金政策的一群学生为例,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会从乌合之众转化为一个组织呢?乌合之众是一个集体,是一起奔走呼吁、到处乱转之人的集体,但它不能以自身的名义做出决策或采取行动,并且边界模糊不清。从乌合之众转化为一个组织需要满足下述3个条件:
· 制定集体一致同意的、代表集体的决策程序;
· 授予个体代表集体行动的权力;
· 确定集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
在满足这3个条件的情况下,集体的成员开始转化为明确的“我们”,可以做出集体决策并落实行动。
当乌合之众的成员转变为集体决策的执行者和集体行动的承载者时,他们就组成了古希腊语中的城邦(polis)。由于集体须作为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ies)才能采取组织行动,因此组织必须首先具有政治性,然后才能表现出其他性质。接下来就是个体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而且他们代表的是集体,是集体的行动者。为了让个体顺利地以集体的名义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就必须有确定集体边界的规则。只要集体的成员创设了此类规则,我们称之为“组织规章”,集体就转化成了城邦,那就意味着个体成员被组织起来了。
缔造组织所需的规章不一定是有意制定的,也不一定要非常明确,重点在于它能约束成员的行为。如果那些在校长办公室外聚集的学生懂得如何组织起来,那么他们就会自发制定有关决策、授权、成员资格的规章。大家可能对此心照不宣,除非有让他们产生疑问的事情发生,比如发生意外和危机或有新成员加入,否则就没必要明文规定规章内容。只要约束个体成员行为的规章具有连续性,那么即使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老成员退出,组织仍会继续存在。组织的存在未必会因为这些规章中存在的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或前后不一致而受到损害,有时反而可能会得到巩固。
通过制定规章来进行决策、授权和确定成员资格,集体就转变为具有行动能力的组织。但如果我们希望把这种组织行动理论应用于常见的社会组织,就必须进一步辨析。
那些学生可能组建了一个仅存在于抗议时期的临时组织,当校长同意召开一次全校范围的助学金会议后,该组织就会自动解散。詹弗朗切斯科·兰扎拉(Gian-Francesco Lanzara)用“短暂组织”(ephemeral)来称呼这类临时性非正式组织。短暂组织可能是人们为了应对一场危机而自发组建的,比如兰扎拉提到的应对意大利南部阿布鲁齐地区地震的组织,它们一夜之间突然涌现,救灾结束后又迅速解散。然而,在一段时期内,这些组织能够作为协作系统发挥作用。
正如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所指出的,组织隶属于系统,它可以让个体在该系统中相互协作,执行重复出现的任务,如煮咖啡并分发给震区灾民。每个协作系统都会根据某些原则,采用一种策略来划分其定期执行的任务,并把划分好的任务委托给个体成员,从而发挥组织的作用。组织的“任务系统”就是相互关联的角色模式,它既是一种劳动分工,又是一种提高工作绩效的设计。这种设计与其他工艺品设计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涉及多种变量、价值观与约束条件;具有变异和变化的倾向;可能会在实施之前就正式提出,即“预先计划”,也可能会在实施的同时进行,或者干脆重新设计。
“常设组织”(agency)也是个体的集合,但不同于短暂组织,它能够持续做出决策、授权采取行动并监督成员资格。常设组织还是定期执行重复性任务的集体工具。家庭是一种典型的常设组织,民间社会中个体组成的持久性协作系统也是常设组织。例如,阿米什人会组成协作建筑队,定期接受建造房屋、筒仓或牲口棚等任务。这类团队通常没有正式的计划或明确的领导者,仅仅在现场的建筑材料前通过谈话和手势等构建具体的任务系统。这种非正式的常设组织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表明在文化上存在所有成员都熟悉的特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不断复制,进而以各种面貌出现。
常设组织还包括更常见的组织实体,如企业、教会、学校、军队、工厂、工会、社会服务机构、政府机构等。这些都是正式组织,其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明确的,并以社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这类组织被正式确认为法人,其任务系统比较复杂,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官僚机构的特征:个体与其组织角色之间有着明确区分、对角色和规章有详细的描述、任务系统程序化、权力结构等级分明并呈金字塔式等。这类复杂的任务系统既可能是紧密耦合的,也可能是松散结合的;既可能是刚性的,也可能是弹性的。然而,所有这些都符合我们对组织行动条件的基本界定,即它们是受城邦的组织规章约束的协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