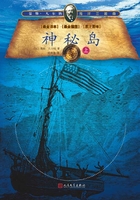
第4章
石蛏——河口的河流——“烟囱”——继续寻找——绿树林——储备燃料——等待退潮——从海岸高处——木筏——返回海滩
首先,记者叫水手在原地等他,说他会回来找他们,然后便刻不容缓地朝着黑人纳布几小时前去的那个方向,沿海岸而上,接着很快消失在海岸的一个角的后面,因为他急于要得到工程师的消息。
哈伯特本想陪他一起去。
“留下吧,小伙子,”水手对他说,“我们得准备一个宿营地,还得看看是否能找到某种可往嘴里送的东西,宿营地比贝壳坚实一些才是。我们的朋友回来后需要恢复体力。各有各的任务嘛。”
“我准备接受任务,彭克洛夫。”哈伯特答道。
“好!”水手又说道,“说干就干。让我们一步步来。我们又累、又冷、又饿,所以嘛,重要的是要找个住处,生堆火,弄点吃的。森林里有木头,鸟巢里有蛋,剩下的就是找栖身之处了。”
“好吧,”哈伯特答道,“我到这些岩石中去找个洞穴,我最终会找到一个我们能钻得进去的。”
“说得是,”彭克洛夫答道,“上路吧,小伙子。”
瞧,他们两人走在了巨大的峭壁下,落下的海浪使之充分露出在海滩上。可是,他们并没有北上,而是南下了。彭克洛夫早已注意到,在离他们上岸地点下方几百步处,海岸呈现出一个狭窄的豁口,据他看来,这该是一条河或一条小溪的出口。一方面,在可饮用的水流附近安营扎寨很重要,而另一方面,水流会把赛勒斯·史密斯冲到这边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前面已经说过,这悬崖峭壁高达三千英尺,可这整块岩石到处都是满的,哪怕是在它的底部,在海水几乎能舔到之处,也没有丝毫能充当临时住所的缝隙。这是一种垂直状峭壁,由非常坚硬的花岗岩构成,而海浪从未能侵蚀它。在接近顶部之处,整整一群水鸟在飞来飞去,尤其有各种蹼足类鸟,它们的喙又长、又扁、又尖——这类鸟爱瞎叫唤,见到有人在场并不怎么害怕,而也许这是人类初次打扰它们的清静。在这些蹼足类鸟中,彭克洛夫认出了好几只海鸥类的拉贝贼鸥,它们有时被称作贼鸥,还认出了一些贪吃的小海鸥,它们在花岗岩的凹处搭窝筑巢。要是朝这一大群鸟儿开上一枪,没准能打下不少,可要想开一枪,就得有支枪,而彭克洛夫和哈伯特都没有。再说,这些海鸥和贼鸥几乎不可食,就连它们的蛋,味道也很差。
这时,已在左边多走了几步的哈伯特,很快就示意有几块岩石上覆盖着海藻,而几小时后,上涨的海水会将它们淹没。在这些岩石上,在滑溜溜的海藻中间,充斥着许多双瓣贝类动物,而饥肠辘辘的人是不会轻视它们的。于是哈伯特叫了一声彭克洛夫,那位赶紧跑了过去。
“哟!这是贻贝!”水手嚷道,“这下可有东西代替我们正缺的鸟蛋了!”
“这并不是贻贝,”哈伯特答道,他正在专注地观察附着在岩石上的软体动物,“这是石蛏。”
“这东西能吃吗?”彭克洛夫问道。
“当然能。”哈伯特答道。
“那好,我们就吃石蛏吧。”
在这方面,水手可以信赖哈伯特。小伙子在博物学方面很棒,而且对这门科学始终有着真正的迷恋。是他父亲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并让他去听波士顿最出色的教授们的课程,而那些教授们都很喜爱这个聪明勤奋的学生。因此,他那博物学爱好者的本能,以后将不止一次地得到利用,而他一开始就没弄错。
这些石蛏是一种椭圆形的贝类动物,它们成串地,而且很黏地附着在岩石上。它们属于钻孔类软体动物,这类软体动物能在最坚硬的石头上打洞,而它们的外壳两端呈圆形,这一特征在一般的贻贝中是看不到的。
彭克洛夫和哈伯特饱餐了一顿这些石蛏,它们的壳,当时在阳光下半开着。他们像吃牡蛎一样地吃它们,并觉得它们有一股很浓的辛辣味,于是他们不再为没有胡椒和任何的调味品而感到遗憾。
他们的饥饿状态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口渴还是照样,而且在吃了这些本身带有辛辣味的软体动物后,口渴得更厉害了。问题在于要找到淡水,而在这样一个地形如此起伏多变的地区,要说是缺淡水,像是不大可能的。为谨慎起见,彭克洛夫和哈伯特采集了大量的石蛏,把口袋和手帕装得满满的,然后便回到了高地下面。
走出了两百步,他们来到了那个河口,根据彭克洛夫的预感,有条小河大概会由此处滔滔不绝地流出。在这个地方,峭壁像是曾经被某种强烈的火的力量分开过。在它的底部,有一个深凹进去的小海湾,而湾底构成了一个相当尖的角。那里的水流有一百英尺宽,而其两边的陡岸,每边仅二十英尺。小河几乎是直接地扎在这两座花岗岩壁之间,而这两座岩壁,在河口的上游呈下降趋势,然后它突然拐弯,消失在半海里处的一片矮林下。
“这里,有水!那里,有木头!”彭克洛夫说,“得,哈伯特,就只缺住处了!”
河水是清澈的。水手看出,潮水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当海水低落,上升的波浪达不到它那儿时,它是淡的。这个重要的问题一旦解决,哈伯特便寻找起某个可充当藏身之处的洞穴来。但他白找了。哪儿的峭壁都是光滑的、平坦的、垂直的。
然而,就在水流的那个河口,在被上涨的海水轮番冲击之处的上面,崩塌的岩石虽没有形成一个岩洞,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岩石堆,这种岩石堆在花岗岩地区常可见到,素有“烟囱”之称。
彭克洛夫和哈伯特相当深入地进到岩石之间,进到那些铺沙的过道里,那里不乏阳光,因为它是通过花岗岩之间留出的空隙射进来的,其中有些仅靠奇迹般的平衡保持着一定的状态。可随着阳光一起进来的还有风——一种真正的穿堂风,而随着风一起进来的,是外面的刺骨的严寒。但是水手认为,堵住这些过道的某些部位,用沙石的混合物堵住某些开口,就可将“烟囱”变得能够住人。它们的几何图形相当于活版印刷符号&,即拉丁文词“等等”的缩写形式。然而,使符号上面那个进南风和西风的环形部分隔热,大概就可利用它的下面部分了。
“这就是我们的事了,”彭克洛夫说,“万一我们能再见到史密斯先生,他会利用这座迷宫的。”
“我们一定会再见到他的,彭克洛夫,”哈伯特大声说道,“等他回来时,他也一定会发现这里有个大致还过得去的住所。这样的住所会好的,假如我们在左边的过道里安个炉子,再在那里留个出烟口的话。”
“这我们能办到,小伙子,”水手答道,“而这些‘烟囱’(这是彭克洛夫为这临时住所保留的名称)将由我们来处理。不过首先,我们去找些燃料吧。我想,要想堵住这些开口,木头对我们不会没用,而魔鬼在通过这些开口吹喇叭呢!”
哈伯特和彭克洛夫离开了“烟囱”,绕过拐角后,他们开始沿河流的左岸而上。水流相当湍急,顺流冲走了几根枯木。上涨的潮水——此时已可感觉到——想必会把这股水推出相当远的距离。水手于是认为,可利用潮涨潮落来运送重物。
走了一刻钟后,水手和小伙子来到了一个突然出现的拐角,那是河流向左拐去时形成的。从此处起,水流穿过一片树木长势极好的森林继续往前。这些树木保留了它们的绿色,尽管生长的季节快要结束,因为它们属于针叶类。这类树遍布地球上的各个地区,从北方的气候直到热带地区。年轻的博物学家尤其认出了“德奥达尔”,这是一种在喜马拉雅地区大量生长的树,它们散发出一种宜人的芳香!在这些美丽的树木间,生长着一丛丛松树,其不透光的太阳伞敞开着。彭克洛夫觉得自己的脚踩断了枯树枝,它们噼啪作响,如鞭炮一般。
“得,小伙子,”他对哈伯特说,“我虽然不知道这些树的名称,可我起码知道把它们归入‘可燃木’之列,眼下,这可是唯一适合我们的树木!”
“那就让我们来储备燃料吧!”哈伯特回答道,同时马上就干开了。
收集工作并不难。甚至无需损伤树木,因为大量的枯树枝就躺在他们的脚下。可是,燃料虽不缺,运输工具却让人渴求。这些树枝非常干燥,因而想必燃烧迅速。所以,必须把数量可观的树枝带回烟囱去,光靠两个人干是不够的。哈伯特指出了这一点。
“嗨!小伙子,”水手回答道,“得有一个运送这些木头的方法。不论干什么,总得有方法才行。假如我们有辆大车或有条船,那可就太方便了。”
“可我们有河呀!”哈伯特说。
“说得对,”彭克洛夫回答,“河对我们来说将是一条自己会走的路,而木筏也不是白白地被发明出来的。”
“只是,”哈伯特提醒道,“我们这条路此时所走的方向,与我们所走的方向恰恰相反,因为海水上涨了嘛!”
“等海水落下,我们就摆脱困境了,”水手回答,“而且将由它来把我们的燃料运回‘烟囱’去。我们只管准备木筏便是。”
水手朝森林边缘和河流形成的那个角走去,哈伯特尾随其后。两人都按照自己的体力,扛了一些捆扎好的木头。陡峭的河岸上也有大量枯树枝在草丛里,而这草丛,人的脚可能从未大胆踏进过。
在由河岸岬角产生的、击碎水流的旋涡中,水手和小伙子放了一些相当粗大的、被他们用干藤捆扎在一起的木段,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木筏,全部的收获——起码相当于二十个人的负荷——被连续不断地堆了上去。一个小时后,工作完毕了,而木筏停泊在陡峭的河岸边,须等潮汐交替方可出发。
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彭克洛夫和哈伯特经过商量,决定到上面的高地去,以便在更广的范围内观察一下该地区。
在河流形成的那个拐角后面走出两百米,正巧有座峭壁止于岩石的崩塌,其结束部分在森林的边缘呈缓坡形。这就好比一座天然楼梯。哈伯特和水手于是开始攀登。多亏双腿有劲,片刻工夫他们就到达了峰顶,并来到它在河流的出口上面所形成的拐角处。
一到那里,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太平洋,那是他们刚刚在十分可怕的条件下穿越的!他们心情激动地注视着海岸北面的那个部分,那正是出事地点,是赛勒斯·史密斯的失踪之地。他们用目光搜寻了一番,看是否有气球的残骸,因为有可能曾有个人紧紧地抓住过它。什么也没有!大海只是荒漠般的一片浩瀚之水。至于海岸,则同样荒无人烟,不论是记者还是纳布,都踪影全无。也可能这两人此时所在的距离,使得别人无法瞥见他们。
“我觉得,”哈伯特大声说道,“像赛勒斯先生那样坚毅的人,是不会轻易让自己被淹死的。他大概已到了海滩的某一处。对不对,彭克洛夫?”
水手忧伤地摇了摇头。他对再见到赛勒斯·史密斯几乎已不抱希望,可是他愿意留给哈伯特某种希望:
“有可能,有可能,”他说,“我们的工程师是个能摆脱困境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换个人也许就没命了!……”
此时,他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海岸。只见眼前沙滩一片,直到被一排岩礁挡住为止。这些仍然露出在水面的岩石,仿佛一群群水陆两栖怪物似的,卧在拍岸浪里。在礁石带外面,大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南面,有个尖尖的岬头形成了地平线,于是无法辨认,陆地是在往该方向延伸,还是在往东南方向或西南方向延伸,如果是,这片海岸就成了一种拉得很长的半岛。在小海湾的北端,海岸的轮廓线继续延伸了很长距离,而这线条比较圆。在那里,海滩低矮、平坦,无悬崖峭壁,有大片的沙洲,那是落潮后露出的。
彭克洛夫和哈伯特于是转身朝西望去。他们首先留意到了那座顶部覆盖着白雪的山,它耸立在六七海里处。从它最初的斜坡起,直到离海岸两海里处,只见大片大片的树群连绵不断,而大片的绿色则使其格外突出,那是因为其中有常绿树。接着,从这片森林的边缘起直至海岸,是一片青葱翠绿的宽阔高地,上面长满一丛丛分布随意的树。在左边,透过林中空地,可不时地看见河水在闪烁,它那相当蜿蜒的水流又把它带到山梁的分支,而在分支之间,大概有它的源头。在水手放木筏的地点,它开始在两排高高的花岗岩壁之间流淌。可是,如果说在其左岸石壁始终是光洁而陡峭的,那么在右岸则相反,它逐渐变化,岩石堆变成孤立的岩石,岩石变成石子,石子又变成鹅卵石,直到岬角的尽头。
“我们是在一个岛上吗?”水手喃喃地说。
“不管怎样,它好像是挺大的!”小伙子回答。
“一个岛,哪怕是再大,也终归只是个岛而已!”彭克洛夫说。
可这个重要的问题目前尚不能得到解答。它的答案得推迟到另一个时刻,至于陆地本身,不管是岛还是大陆,看起来土壤是肥沃的,景色是宜人的,出产是多样化的。
“这可真是万幸!”彭克洛夫道,“而我们在困境中,应当为此感谢上苍。”
“谢天谢地!”哈伯特答道,他那颗虔诚的心,对造物主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这个命运把他们抛入的地区,他们观察了很久,可是,光这么粗略地观察一番,要想象他们将来会怎样,还是困难的。
然后,他们沿着花岗岩高地南面的山脊返回,这山脊是由一长排的不规则岩石组成,它们具有最稀奇古怪的形状。在那里,有数百只鸟儿栖息在石洞里。哈伯特跳到岩石上,吓跑了这些飞禽中的整整一群。
“啊!”他嚷道,“这些鸟既不是海鸥,也不是隼鸟!”
“那它们是什么鸟?”彭克洛夫问道,“说真的,像是些鸽子!”
“的确是鸽子,不过是野鸽,或原鸽,”哈伯特答道,“我认得出,看它们翅膀上的两道宽宽的黑条纹、白色的尾部、青灰色的羽毛便可。然而,要说原鸽的肉好吃,那它的蛋,想必味道也是鲜美的。只要它们稍微在窝里留点就行!……”
“我们可不会给它们时间来孵蛋,除非它们孵出来的是煎蛋!”彭克洛夫兴高采烈地回答。
“可你用什么来做煎蛋呢?”哈伯特问道,“用你的帽子吗?”
“得啦,”水手回答,“我可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只好吃煮蛋了,小伙子,而那些最硬的,就由我来负责处理好了!”
彭克洛夫和小伙子认真察看了一番花岗岩的凹处,而他们果真在某些洞里找到了一些!拾了几打后,便装在水手的手帕里,等海水该满潮的时刻一临近,哈伯特和彭克洛夫便开始朝水流方向下去。
当他们到达河流的拐弯处时,时间是午后一点。水流已在反向流淌。所以,得利用退潮把木筏带到河口去。彭克洛夫无意让这木筏毫无方向地随流而去,也不打算上去驾驭它。可一名水手,一旦涉及缆绳或绳索之类时,从来就难不倒。彭克洛夫飞快地用干藤编了一根长好几英寻的长绳。这根植物缆绳被拴在了木筏后面,水手用手拉着它,而哈伯特用一根长竿推着木筏,就这样把它维持在水流中。
一如所希望的,此举成功了。由水手在岸上边走边控制着,大量的木头顺流而下。河岸十分陡峭,无需担心木筏会搁浅。两点前,它到达河口,那里离“烟囱”仅几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