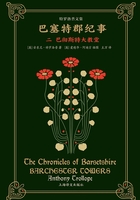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7章 教长与牧师会会商
全巴彻斯特群情鼎沸。格伦雷博士还没有走出大教堂门廊,便愤怒地发作起来了。年老的教长静悄悄地回到他的公馆去,一句话也没敢说。他到那儿坐下,惊吓得有点儿发呆,白费脑力地默想着许多事情。哈定先生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走去,缓缓地走过教堂区的榆树下面,几乎无法使自己相信方才听到的话,会是从巴彻斯特大教堂的讲道台上发出来的。他会再受到打扰吗?他的全部生活会再一次给人揭露出来,说成是一场无益的骗人的经历吗?他会不会非得放弃他的领唱人职务,像放弃院长职务那样,并且抛开唱歌,像抛开他的十二个老受施人那样呢?要是他当真非得这样,那怎么办呢?另一份《朱庇特日报》[101],另一位斯洛普先生会出面来,把他撵出圣喀思伯特教堂。他一辈子像他所做的那样唱连祷,谅必总不会错!然而,他开始有所怀疑。自我怀疑本是哈定先生的弱点。不过,这并不是他这个阶层的人通常的过失。
不错!全巴彻斯特群情鼎沸。受到影响的并不只是教士。世俗人士也听到了斯洛普先生的新教义,大伙儿全感到很惊讶,有些人感到很愤慨,有些人则带着复杂的情绪,他们中对讲道人的厌恶倒不是十分强烈的。老主教和他的牧师们,教长和他的驻堂牧师与低级驻堂牧师,过去的唱诗班,特别是领唱的哈定先生,以前在巴彻斯特全很受欢迎。他们花自己的钱,做了一些善事。穷人并没有遭到压迫,社会上的教士既不专横,也不苛刻。这座城市享有的声誉,完全是由于它在教会中的重要性。然而,也有些人听完了斯洛普先生的讲道,感到很满意。
我们对单调的日常生活深感厌烦时,受到一点儿使人兴奋的刺激是十分愉快的!圣歌和《谢恩赞美歌》本身就是令人欢畅的,但是人们经常听到它们!斯洛普先生无疑是令人讨厌的,但他是新来的,而且很机灵。他们早就认为,如同许多巴彻斯特人这时候所说的,像过去那样单调乏味地生活下去,压根儿不去听使外界激动的那些宗教改革,那是迟钝的。走到时代前面的人,这时候有些新思想,而巴彻斯特应该走在前面,这已经是时候了。斯洛普先生的话也许是对的。礼拜日在巴彻斯特的确没有受到严格的遵守,只有大教堂里举行的礼拜式除外。说真的,礼拜式之间的那两小时,早就给用在午后探亲访友和吃一餐热和的午饭了。再说主日学校!实际上是该为主日学校再多做点儿事。斯洛普先生管它们叫安息日学校。已故的主教实在没有像该做的那样考虑到主日学校。(这些人大概没有想到,教义问答和短祷告对年轻人来说,就像簿记对年长的人那样,是很辛苦的工作。在一项工作里和另一项工作里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做礼拜的情绪。)再说,关于礼拜式的音乐这个重大问题,站在斯洛普先生那方面,也许是有不少话可说。当然,人们上大教堂去听音乐等等等等,这也是事实。
因此,一个站在斯洛普先生那面看待这问题的团体,确实在巴彻斯特形成了!这在上层社会主要是一些妇女。没有一个男人——那就是说,没有一个有身份的男人——会给斯洛普先生吸引住,或者同意追随如此令人厌恶的一个迦玛列[102]。妇女们在评定身体合格不合格方面,往往不十分细致。只要一个人对她们讲得不错,她们就倾听,虽然这是从一张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畸形、丑恶的嘴里讲出来的。威尔克斯[103]作为一个情人是极其幸运的,而这个湿乎乎的、沙黄色头发、滚圆的大眼睛、紧握着充血的两手的斯洛普先生,就只对女性的情绪具有影响力。
然而,附近的教士中有一两个人却认为,忽视了眼下贮藏着巴彻斯特主教区的饼和鱼的篮子[104],是不十分安全的。他们,也只有他们,在斯洛普先生登上大教堂讲道台“表演”完毕后,连忙去拜访了他。这些人里有布丁谷的教区长奎瓦富先生[105],他的妻子一年年还继续奉献给他新的爱的结晶,从而增加了他的忧虑,同时我们希望,也增加了他的幸福。一位先生膝下有十四个活生生的儿女,每年只有四百镑收入,就连在饼和鱼到了斯洛普先生的支配下,也只好去谋求它们,这一点有谁会感到惊讶呢?
在这次讲道的那个星期日过去后不久,附近一带的主要教士就应当如何抑制斯洛普先生,举行了激烈的辩论。首先,决不能让他再站到巴彻斯特大教堂的讲道台上讲道了。这是格伦雷博士最初提出的意见,他们全同意了,只要他们有权把他排斥在外的话。格伦雷博士宣布说,权力掌握在教长和牧师会的手里,说牧师会以外的牧师没有一个有权在那儿讲道,只有主教本人除外。对这个意见,教长表示同意,不过他指出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争论将是不合式的。对这句话,一位瘦小的博士,大教堂受俸牧师之一,回答说,如果所有的牧师都经常待在那儿准备自行站上讲台,那么反驳就必然完全在斯洛普先生一方了。瘦小、诡诈的博士啊!他住在巴彻斯特大教堂区内自己的舒适的住宅里很合意,所以心满意足地稍稍来攻击一下维舍·斯坦霍普博士和其他缺席的人了,他们的意大利别墅或是伦敦的迷人的住宅,的确要比大教堂的牧师席位和牧师公馆更具有吸引力。
那个粗壮结实的大教堂司铎是一个沉默寡言,但又通情达理的人。对于这话,他回答说,缺席的受俸牧师都有他们的教区牧师[106],而在这种情况下,教区牧师登上讲台的权利,和较高一级牧师的完全一样。教长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内心里为这些实情苦哼了一声。但是关于这一点,瘦博士却说,这些权利将落到低级驻堂牧师的手里,其中有一个也许随时都会辜负他所受到的委托。这当儿,只听见那个粗壮结实的大教堂司铎喊了一声,听来有点儿像“呸,呸,呸”,不过也可能那位可敬的先生仅仅是从气管里喷出沉重的呼吸来。干吗不让他说话呢?哈定先生这么说。让他们毫不羞惭地听听随便谁可能要向他们讲的话,除非他讲的是虚伪的学说。如果是那样,那么让主教叫他不要说。我们的朋友这样讲,这可是白费,因为人类的目的必须通过人类的手段来达到。但是教长从他那双昏花的老眼里却看出了一线希望。是的,让他们告诉主教他们多么厌恶这个斯洛普先生,一位新主教刚来就职,决不会希望在他的第一件长坎肩还簇新的时候,就来侮辱他的牧师。
这时,格伦雷博士一下子站起身来了。他这样收集了他的团体内一鳞半爪的智慧以后,用富有权威性的措辞开口讲话了。当我说会吏长一下子站起身来,我指的是他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当时一跃而起,采取了更为直接的行动。实际上,博士的身子一直都站在那儿,背对着教长的空壁炉格,长礼服的燕尾支撑着他的两只胳膊,两手全插在裤子口袋里。
“很清楚,决不可以再让这个人在这座大教堂里讲道了。我们全看清了这一点,除了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107],他的性情那么温和,因此不忍心拒绝罗马教皇不出借他的讲道台,如果罗马教皇果真要来借用的话。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让这个人再在这儿讲道了。不是因为他对教会事务的见解跟我们的可能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会争吵的——而是因为他故意侮辱我们。上个星期日他登上讲道台时,蓄意就是要来冒犯一下一些老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很崇敬的一些事情,他竟敢那么轻蔑地讲到。怎么!作为一个陌生人,一个没有名声、没人理睬的年轻陌生人,跑到这儿来,以他主子主教的名义告诉我们,我们不懂自己的职守,保守、过时、毫无用处!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最钦佩他的勇气呢,还是他的冒失无礼!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那篇讲道文完全出自那家伙本人。主教就和眼下在这儿的教长一样,根本没有参加进去。普劳迪博士凭借那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使自己很惹人注目,你们全知道我看见这个主教区的主教就抱着这样的见解,心里觉得多么悲痛。你们全知道我多么不信任这样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我相信普劳迪博士在上流人士中生活了好多年,决不会犯下,或是煽动别人去犯下这么严重的一个粗暴行为的。不会!那个人暗示他是作为主教的代言人发言的,他这么说是不真实的。他马上就来向我们挑战,这是很符合他的野心勃勃的观点的。他就在这儿,在我们安安静静地尽着自己的宗教职责时——在我们心爱的大教堂里面——在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和和睦睦、声名卓著地行使着我们牧师职务的这儿,公然很快来向我们挑战。从这样一个方面来对我们作这样一次攻击是十分可恶的。”
“十分可恶的。”教长苦哼了一声。“十分可恶的,”瘦博士嘟哝说。“十分可恶的。”大教堂司铎应和了一声,从丹田里发出他的声音来。“我实在也认为是这样。”哈定先生说。
“最最可恶、最最没有来由的,”会吏长说下去,“可是教长先生,谢谢上帝,那个讲道台还是我们自己的:我得说,是你们自己的。那个讲道台完全属于巴彻斯特大教堂的教长和牧师会。到目前为止,斯洛普先生还不是这个牧师会的一分子。您,教长先生,曾经建议我们应该去向主教呼吁,请他不要把这个人强加给我们,但是如果主教听凭自己被他的家庭牧师所支配,那怎么办呢?依我看来,这件事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斯洛普先生不请求许可,不得到许可,就不能在那儿讲道,那么就让他永远得不到许可吧。凡是他想要参加大教堂礼拜式牧师工作的要求,我们都拒不同意。如果主教决意要来干涉,那么我们就知道该怎样答复主教了。这位朋友方才说,这个人接受下您的某一个低级驻堂牧师的职务以后,也许会再一次设法登上讲道台,可是我相信,当大伙儿都知道教长反对任何这样的调动时,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些先生们会支持我们的。”
“你当然可以相信了。”大教堂司铎说。
这些有学问的人举行的这次秘密会议,接下去又进行了更多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听从了会吏长的指示。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习惯于他的管理,所以无法这么快就摆脱掉他,而在当前的这件事情上,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希望去帮助会吏长这么急切地想要压制下的那个人。
我们刚记载下的这样一次会议,在巴彻斯特那样一个城市里举行,是不会不为人知、不为人传的。在每一所体面的宅子里,包括主教公馆在内,不仅是这次会议给人谈论着,而且教长、会吏长和大教堂司铎的讲话全给复述着,还按照讲述者个人的爱好与意见,作了许多增添和无中生有的描绘。
然而,大伙儿一致同意说,应当阻止斯洛普先生在巴彻斯特的大教堂里再开口说话了。许多人认为,守堂的执事应当奉命甚至拒绝给他安排一个座位。有些主张采用过激措施的人扬言说,他的讲道文应当给看作是一项可加控诉的罪行,而且还将以喧闹罪对他提起公诉。
那些想为他辩护的人——那些热心而虔诚的年轻妇女和那些渴望有所行动的中年处女——当然为了这次攻击更加热情地替他辩护。如果她们在大教堂里没法听到斯洛普先生讲道,她们就上别地方去听。她们就撇下那个单调乏味的教长、那些单调乏味的老牧师,以及那些几乎同样单调乏味的年轻的低级驻堂牧师去听他们彼此讲道。她们将替斯洛普先生做鞋子和椅垫,还要为他镶宽领带[108],把他变成一个快乐的殉道者,树立在一所新的独立教堂[109]内,使大教堂变得完全不合时宜。
普劳迪博士和夫人立即返回伦敦去。他们认为在这场迅猛的风暴过去以前,避开教长和牧师会提出的关于那篇讲道文的任何个人请求,是得计的。可是他们让斯洛普先生无所畏惧地留了下来。他热心地从事着他的工作,对那些乐意听他奉承的人大加奉承,对傻呵呵的女人小声说上一些宗教废话,讨好那少数几个肯接待他的牧师,访问贫民的家庭,调查所有的人,件件事全去探听,用最精细的目光寻找公馆内所有损坏的地方。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试图再在大教堂里讲道。
这样,全巴彻斯特都争吵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