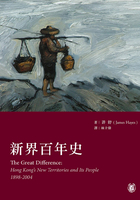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高馬可序
許舒對香港的新界瞭如指掌,在這方面能與他相埒的學者屈指可數。許舒在2006年版《新界百年史》的序言中說,他看待這個地區的事件時,總是從兩個角度出發:一是政府官員的角度,另外是歷史學家的角度。這種眼光令他能整體地看新界,而非只聚焦於某個鄉村。不過,許舒的研究最顯著的特點,在於他致力探討的是新界本身,而不是像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70年代末中國「開放」前許多人類學家那樣——是為了解「傳統」中國農村社會。許多「農村研究」常見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也不見於許舒的著作中。雖然他承認自己偏愛新界鄉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但《新界百年史》是翔實和平衡的研究,探討新界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情況,並不是為號召大家起來支持所謂的「原居民」社群。
《新界百年史》最主要論述的是變遷。例如許舒記述了客家話的衰落,他注意到以粵語和英文為主的公共教育普及後,客家話變成主要在家中使用。在南丫島,村民的生計到了1950年代末從近岸捕魚變為養豬。在大嶼山的貝澳,新道路和巴士服務帶來更多城市人和度假屋,而歐籍人士則開始經營餐廳和咖啡館。對許多村民來說,由1920年代起至1970年代為興建水塘而大量搬遷和重置鄉村的計劃,令山川景物和生活方式徹底改變。移民海外(主要是英國)也對鄉村造成深遠影響。到了1980年代末,新界某些地區與香港其他部分,已經幾乎看不出有太大差異。
許舒指出1980年代初新界的勢力平衡如何開始變化,尤其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個地區甚至直到今天的政治動態。推行地方選區投票,以及來自市區公共屋邨和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壯大,造就了新類型的地區領袖。區議會全面直選後,能夠保住權力的原居民寥寥無幾。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有關原居民權益的爭議令許舒為之慨嘆,他歸咎於鄉民的保守思想和城市人對新界的無知。到了新界租約終結之時,許多非鄉民在新界擁有或租住房屋,在某些地區,人數甚至比原居民還要多。
此書也可說是關於殖民主義的著作,殖民主義這個成分,在許多有關新界的「中國性質」(Chineseness)的研究中付諸闕如。殖民地政府高官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在1898年8月調查過這片新租借地歸來後,用「巨大差異」來形容新界居民與香港居民之間的鴻溝。當時英國人佔領香港已超過五十年,駱克十分清楚新界與香港之間的差異,以及這可能為殖民地政府帶來的問題。新界領袖在1899年大力反抗英國統治(這是夏思義[Patrick Hase]的《被遺忘的六日戰爭》的主題,也是由中華書局翻譯出版),但政府還是決定依賴地方領袖,許舒歸功於總督卜力(Henry Blake)。在愛爾蘭當過警察和常駐裁判官的港督卜力,在武裝反抗平息後決意專程與那些地方領袖親身會面。在1899年末開始的首次土地丈量,自然也有深厚的殖民聯繫——執行這項工作的人,是從印度測量局借調來的歐籍和印籍人員。
如許舒在2006年版的序言所說,對於撰寫《新界百年史》的辛勞,他「甘之如飴」並希望藉此「稍為回報香港帶給我的一切」。香港人——無論是鄉民還是城市人,無論是土生土長的人還是初來乍到的人——全都應感激許舒,因為他提供了關於這個迷人地區豐富多采的記述。
高馬可(John M. Carr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