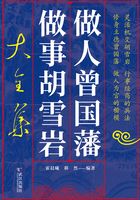
第4章 刚柔并用,审时度势
天地之道,刚柔并用,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事情都有刚柔不同的两方面,任意一方都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有智慧的人往往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好取舍,掌握好自己的度,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圆融地通行于不同的力量之间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都不求极致,留下余地,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游刃有余。
4.1 委婉圆柔达成目的
天地之道,刚柔并用,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事情都有刚柔不同的两方面,任意一方都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有智慧的人往往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做好取舍,掌握好自己的度,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圆融地通行于不同的力量之间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都不求极致,留下余地,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游刃有余。
曾国藩对于刚柔并济的做人之道深有体会,他所处的环境中不仅要面对自己的同僚,更要时时刻刻小心地应付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掌握着生杀大权,随时都可以让伴君者灰飞烟灭。之所以处于这种境地的曾国藩仕途依旧平坦,正是因为他掌握好了与帝王相处的度。
咸丰年间,曾国藩曾经居丧在家,这一阶段他获得了难得的清净,可以耐心地思考很多问题,让他贯彻了很多从前不明的智慧。而在这一时期他也犯过一个大错误,差点让自己一生的前途都断送掉,那便是他主动伸手向朝廷要官。此事令清廷的统治者大为光火,认为曾国藩野心外露,幸而他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此举已经越界,因此及时挽回,才得以保住了自己的仕途。
此事之后,曾国藩一直都深刻地反省自己,经常拿此事来提醒自己一定要掌控好做事的度。至晚年时,他更是深刻检讨了自己当时的“不知进退”,以警醒后人。从这件事上,曾国藩顿悟到:“有求于上,应委婉而言”,他明白统治者并不喜欢官员们主动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不仅侵犯到了他们的权威,而且在无形之中夸赞了自己的功绩,形成对于清廷的影响。要想“颇得实惠,步步高升”,掌握好行事的度便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长期的总结之后,曾国藩对于自己和统治者之间的相处之道提出了四条铁律,这也是他的处世经中针对上级领导的基本态度。生杀予夺的皇帝在曾国藩面前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即便曾国藩是难得的将帅之才,有平乱之功,也依旧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因此,曾国藩与皇帝相处的第一态度便是逆来顺受,不管皇帝有任何的责怪,哪怕是误判,都要秉持着恭敬听从的态度,令统治者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尊重,从而减轻对于曾国藩的猜忌。
作为最高统治者,尤其是身处风云突变的乱世,清廷最担心的便是手握重兵的将帅有二心。曾国藩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就算是他权倾一时,属下拥立之心明显,他都没有想过要有越雷池之举,因此他对清廷的态度之二便是:誓死效忠。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曾国藩都在表露自己的忠心,以剔除统治者对自己的不信任。因为他知道一旦统治者的信任消除,任何的职权与荣华也都会随之而去。朝廷可以忍受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品德的官员,而绝对不能忍受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员,效忠是作为臣子的最大原则,也是统治者最为在意的原则。
官场风云诡谲,就算曾国藩对朝廷忠贞不二,对统治者言听计从,也难免会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耿直之士最难忍受的便是一片忠心被无视,而曾国藩却将这种无奈当做是自己为官必须经历的一个部分,不改初衷地认真对待。在他实在无奈之时,便拿出“缓”与“拖”作为应对之策,这也是他对待清廷统治者的第三个基本态度。用“缓”来争取时间,用“拖”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让统治者可以醒悟过来,而曾国藩却可以保全他的原则,不违初衷,又不会与朝廷形成两立之势。
为官但求富贵,是很多人走上仕途的愿望,曾国藩虽然有经世之才,也会有所欲求。因求官而惹恼朝廷,是他过于袒露心愿而招致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逐渐改变了策略,让自己的要求得以满足的同时又不会引起统治者反感,因为他做到了“委婉”二字,这也是曾国藩与统治者相处之道的第四条。
以“委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向朝廷提出要求,需要掌握好言辞与行为的度,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提出愿望,则既能实现目的又能保全彼此体面。
1857年,原属于曾国藩部下的李续宾、杨岳斌统帅着湘军的水陆师,增援湖北胡林翼获得大胜。曾国藩来到九江劳师之后,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应该重新归属回自己调度,同时湘军在战争中也有损耗,朝廷理应给予犒赏。同年一月,曾国藩向朝廷撰写奏章,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愿望。
在奏章中,曾国藩并未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重点说明了三点:其一,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领的水陆师来到湖北的原因,是因为胡林翼告急,自己急人所急,才派遣了部下率军支援。李、杨二人所统领的湘军来到湖北之后,不仅帮助胡林翼收复了武昌,同时还将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收复,建立了赫赫战功。此等勇猛之士正是湘军的战斗力所在,而自己也正需要他们的支持,以此暗示应将李、杨所率领的水陆师拨还给他为湘军。其二,曾国藩丝毫不提自己在收复武昌之中所作的贡献,只是一味地夸赞李续宾、杨岳斌的战功,为旧部脸上贴金,也让朝廷明白李、杨能建此奇功,正是因为有他的指引,从而更加重视湘军的影响力。其三,虽然整个奏章都没有说出自己是李续宾和杨岳斌的领导,但是在奏章的最后,曾国藩却提出要为李续宾、杨岳斌部队请赏,并催军饷。这种态度便是以李、杨二将的指挥者自居,虽不明说,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功劳。
综观这一封奏章,全篇之中没有一处是曾国藩要求朝廷将湘军水陆师拨还,也没有一处是向朝廷说明自己的功绩,但是却通过委婉的方式,让朝廷无法忽视曾国藩在这一场战役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自然不能无视他的要求。曲意示衷令曾国藩也顺利达到了目的,皇帝果然大大嘉奖了曾国藩、李续宾和杨岳斌,同时将部队也重新拨归他来调度,此事成为他以柔克刚之法的一次成功示例,也是他“委婉圆柔”之法的胜利。
4.2 登高才能望远
世事复杂,而官场更为险恶,封建社会的宦海沉浮更隐藏着无限危机,几乎可以算是难有宁日。不管在哪个朝代中,都会有善于钻营、阿谀奉承之徒受到重用,以至于奸佞当道,封建社会的制度决定这种现象不能被根除,那些谋求个人私利的人自然也会不断打压忠贞贤良之辈。曾国藩身处官场,从年轻时代就痛恶那些结党私营的人,而他又不得不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因此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他所在的清王室又是以满清旗人为主,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之心,这更增加了他从政的难度,在这种环境之中,曾国藩不仅做人要小心翼翼,做事更要深思熟虑,唯恐有所不周,当出现困局之时,只有将眼光放长远,才能找到脱离险境的坦途。
曾国藩一直都想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官,因此在根本上就和庸俗的官僚们划清了界限,而他又不希望得罪这样的人而引来闲言碎语,所以不管是说话做事都极为谨慎,有时候就算是吃眼前亏,他也是笑着接受,不做任何抱怨。但对于一些可积累恶习的事,曾国藩却非常明确地坚决反对。
道光年间,在曾国藩家乡任职的朱姓知县,与当地的乡绅们来往很密切,曾家作为当地的名门自然也在其中。而朱知县当政几年之后,当地的财政却出现赤字,面临着被调离的处境。乡绅们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都非常惊恐,因为朱知县的权位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好处,他们不愿意因其调离而危及自身利益。于是有人提议让全县的百姓都来捐钱,用以弥补财政亏空,以便留住父母官。曾家在接到这一通知之后,很快就写信给曾国藩,询问他是否应该参与这一行动。
接到家书之后,曾国藩立刻就回信,告诉家人不要急着参与。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看似为了百姓,其实还是为了自己。虽然倡议的时候个个言辞激烈,许诺愿意多出一份钱,可真正到了掏钱的时候,必然是分摊到百姓头上,至于这些官绅有无掏钱则无从考证了。更重要的是,百姓承担税赋就已经非常辛苦了,而官绅们还要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增加人民的负担。一旦钱收了上来,势必会刺激一些人的贪欲,导致恶官酷吏巧取豪夺的场面,假公济私之下受到伤害的只有百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事一旦有了第一次,以后势必还会有人效仿,官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行这样的措施,岂不是将穷苦的百姓都推进了深渊,以后再也翻不了身了?
基于这种考虑,曾国藩要求家人避免参与此事,同时静观其变,看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而此后因没有人拥戴,这个倡议也就自然落空了。
几十年的官场生涯让曾国藩练就了深谋远虑的本事,更让他可以在遭遇看不惯的事时巧妙地周旋其中。虽然他认为自己非常愚钝,但实际上却非常有心机。不管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的时候,抑或他不得志之时,他都非常巧妙地与朝中的权贵周旋,既不结党营私,又不会成为帮派斗争的牺牲品,因为在曾国藩的眼中,结党的人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
随着功绩的不断建立,曾国藩在清廷之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虽然他不会主动结交权贵,但权贵却不会忽略他。不管是道光年间,还是咸丰年间,以至于慈禧太后把持朝政的同治年间,曾国藩都受到了朝廷权力集团的青睐。道光时的穆彰阿、咸丰朝的肃顺、同治朝的奕訢,他们之间都是属于对立关系,每一次权力的更替都可算是仇人之间的接交,况且穆彰阿和肃顺都未能得到善终。即便如此,曾国藩在三朝之中却和这些人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算穆彰阿和肃顺敌对多年,可当肃顺掌权时,依旧对曾国藩另眼相看。
能够在对立的权力集团之中获得两方面的认可,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曾国藩避开了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而且在肃顺倒台之后,没有留下丝毫与之相交的痕迹。当慈禧太后以政变形式瓦解了肃顺的权力集团后,意图肃清他的党羽,发现朝中的官员都和肃顺有书信往来,唯独曾国藩没有一字一言,找不到任何把柄,就连慈禧都发出了“曾国藩乃忠臣”的感叹。那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历代的权力集团总是不停地更换,曾国藩遍阅史籍自然明了其中的规律,他不愿意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投身于某个权力旋涡之中,变成斗争的牺牲品。从长期来看,任何权力集团都有瓦解的时候,而自己又不能完全地避免,绝对的中立在封建社会的朝廷之中不会存在。因此,曾国藩要一方面取得权贵的信任,一方面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肃顺作为文庆的接班人,在咸丰年间纠结了恰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组成了势力最为庞大的三人集团,深受咸丰帝的信任。他们三人盘结在一起干预朝政,连军机处都要听命于他们,肃顺作为三人的首领又和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结为死党,几乎招纳了朝中所有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一时间风头无两。
在如此大肆结党的环境之中,肃顺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为了长期把持朝政而与慈禧、奕訢等人展开了斗争。对于肃顺来说,军队是尤为关键的力量,湘军又是军队之中战斗力最强的,他自然不会忽视。但就算肃顺在朝廷之中明目张胆地结交权贵,对于作为国家支柱的军队还是不敢贸然行动,因为大臣和手握军权的将帅来往密切最易成为政敌的攻击对象,而曾国藩与胡林翼等人也都巧妙地避嫌,以免引来不测之祸。
事实上,曾国藩表面上和肃顺保持着距离,但却有千丝万缕微妙的联系。因为在肃顺所招纳的众多党羽之中不乏与湘军往来密切的人,有一些湘军集团的人甚至成了肃顺的座上客。在曾国藩做礼部侍郎的时候,尹耕云曾经是他的属员,受到了曾国藩的器重。而其后,尹耕云也担任了肃顺的属吏,并且肃顺还对他“礼敬有加”。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和曾国藩、胡林翼并没有密切来往,但却和尹耕云等关系非同寻常,如高心夔等。肃顺将这些人招揽在门下,除了作为自己的力量来培植之外,还经常与他们共议军政大事。在鸦片战争的战和问题上,肃顺便认真听取了尹耕云、王闿运等人的意见。及至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因其赫赫战功成为当朝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肃顺更加认真地听取着王闿运等人的意见,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而王闿运、尹耕云等在与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信往来之中自然也会商讨当前政事与战况,无形中传达了彼此的态度和意见,形成沟通。
在与肃顺权力集团微妙的关系之下,曾国藩自己也得到了一定益处,肃顺进言咸丰帝,力举并不被咸丰信任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对于曾国藩的一些下属也多有提拔,这无疑是肃顺向湘军集团伸出的友好之手。而曾国藩虽然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实权和利益,但他却一直不动声色,照旧通过一些名士和朋友与肃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并未明目张胆地与其结交。也正是在他这一长远目光的帮助之下,才避免了肃顺倒台之后被慈禧、奕訢集团追绞的厄运。
4.3 让他三尺又何妨
国人进入仕途,多有光耀门楣的愿望,认为只要一人得道,全家自然也就应该升天。对于做官的人来说,通过自己手中的一点权力来为家庭谋取一些额外的福利,似乎也是理所当然。而曾国藩直到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手握当时实力最为强劲的湘军,在朝堂之上一言九鼎之时,也都时刻在要求自己低调为人,从来不愿意因为自身所具备的权力而让家人享受特权。这与他长期以来藏锋守拙的个性有关,也是曾国藩能够在官场纵横多年而不倒的基础。
与“治国、平天下”相比,“齐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治理好一个家庭足以看出一个人的才干。而曾家是一个大家族,不仅人口诸多而且在湖南当地具备着非凡的影响力,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别人的热议。这一切固然是因为曾国藩在朝堂之上的权势,但同时也成为别人观察曾国藩的一个窗口。因此曾国藩对邻里关系相处非常认真谨慎,避免因处理不好关系而产生仇隙,如果制造事端,不但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帮助,还会让近邻变成自己的敌人。而面对这些矛盾,曾国藩所秉持的一个原则便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在同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便是一个谦虚低调的人,他在京城为官,而家人却居住在桐城,他们认为自家在朝中有靠山,难免会有一些跋扈之举,有一次,在修房时和吴姓邻居发生了争执,彼此都不能界定院落的界线。于是张家人便一纸信函发到京城,想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让邻居屈服。张英看到来信之后,莞尔一笑,便手书四句诗寄了回去:“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到了张英的来信,顿时悔悟,依照他的指示在界线上让出了三尺,而邻居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主动让出三尺来,此地便成了闻名古今的“六尺巷”。
此事因《桐城县志》的记载而广为流传,曾国藩认为张英此举正是大智慧,他不会为了一些琐碎之事擅自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更难得的是在与普通百姓发生摩擦时秉持着忍让的精神,身居高位而能做到谦逊,实在难得。及至咸丰初年,曾家因家庭成员众多,需要扩展宅基,也发生了与张英类似的事情,邻居在曾家修建黄金堂时横加阻拦,认为曾家宅基超出了地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一气之下便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要求他发话来摆平不识好歹的邻人。而曾国藩收到书信之后回了一封长信,信中附上了张英的诗作,劝说家中的子弟要心胸开阔,“让他三尺又何妨”?因为这三尺之地,让邻人反目,成曾家恶名,又怎么值得呢?按照他的指示,曾家主动退缩了地界,给邻居方便。而邻人看到曾国藩居然能做到如此忍让,也大受感动,将自家的宅基转让给曾家扩大黄金堂新宅。
不管是在官场上与比自己强势的权贵打交道,还是在乡间与自己的邻居打交道,曾国藩所坚持的原则都是相同的,在无伤原则的时候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这成为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处世秘方。
因曾国藩的教导,曾家的家风一时之间为当地人所称道,曾家的子弟在乡里也成为谦逊的榜样。但由于子弟诸多,其中难免会有依仗权势行恶之徒。曾国藩知道地方官都害怕京官,所以一再告诫自己的家人不要轻易去干预地方官的行政命令。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却一直都听不进去,在乡里横行霸道,多次干预湘乡知县的政事,引起了人们的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各地兴起了“哥老会”,尤其是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原来参与过湘军的人被遣散回乡,大多参加了“哥老会”,形成一定组织为害乡里。曾国潢对于这种组织非常反感,积极参与当地县衙组织的剿灭行动,而他暴躁的脾气在这个过程中日渐增长,遇到了自己憎恶的人就会捆绑到县府之中,要求知县将其判死罪。湘乡县令是一个佛教徒,本以慈悲为怀,但曾国潢家世显赫,每次他有所要求,县令又不敢不从,因此良心受到了极大折磨。有时候曾国潢会一次性捆绑五六十个人,要求县令判死刑,到最后也很难有人生还,县令总是悲戚地说:“曾四借我的手杀人!”
对于家人的所作所为,曾国藩虽然远在京城,但通过书信也略有所闻。他在家信之中多次提及:“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做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提醒子弟就算现在家道强盛,也要时时为将来家道衰落做好准备,千万不要干预公事。尤其告诉曾国潢“人待人为无价之宝”,让他与乡邻处理好关系,不要为恶乡里。但曾国潢并没有因此而收敛,有一年湘乡县新建了一个码头,按照惯例需要宰杀猪牛羊,用“三牲”作为祭礼,但在曾国潢的安排之下,居然杀了十多个人来“血祭”。
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他为了奔丧回到湖南,听说了曾国潢的各种恶行,便想要严厉惩戒他。有一天,曾国潢午睡的时候,曾国藩拿着一个锥子悄悄来到他床边,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被吓醒之后,发现血流满床,被褥都被染红了,顿时大惊失色,厉声责其行为残暴。而曾国藩却说:“我不过是拿锥子刺你几下,你就觉得我残暴,你拿刀杀了人,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你呢?”
经过了这一番“血”的教训,曾国潢暴躁的性格有所收敛,对待乡邻的态度也慢慢好转。曾国藩通过这种行为,让他明白了:与乡邻的相处之中要做到忍让,宽和对待每一个人。
4.4 不计前嫌胸怀广
在波诡云谲之中寻求生存,必须有良好而坚固的人际关系作为基础,这是一条至理。曾国藩身处清廷政治变幻莫测的阶段,历经三朝皇帝,在不断的历练之中也体悟出了自己的为人之道,将这一门深奥的学问钻研得十分透彻。对于自己而言,曾国藩一向都严格要求,不怨天尤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立己达己,而历史上的无数伟人也对此做出了证明。对于别人,曾国藩一向以宽广的胸怀善待之,就算偶尔发生摩擦甚至曾经有过交恶,他都会不计前嫌。这种处世之风让曾国藩的人格魅力获得了大幅度提升,自然也为他吸引了更多的朋友。
与曾国藩同期为官的左宗棠,也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一代将领,他们二人各有功绩,在清廷的眼中都非常重要。而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个性却有很大不同,他对于自身才华非常自信,并且性格耿直,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往往会直言不讳,甚至有一些恃才傲物。曾国藩虽然只比左宗棠大一岁,可是他却为人诚恳老练,平日里谨言慎行,说起话来还稍微显得有些木讷。和言语尖刻的左宗棠比起来,曾国藩显然更受大家的欢迎,而他们二人之间也常有一些小小的摩擦发生。
左宗棠一生经历坎坷,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之后在乡间蛰伏多年,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即便这样,他还是锋芒毕露,丝毫不肯收敛自己的张狂个性。及至咸丰二年(1852),已经四十一岁的左宗棠终于做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脱离了乡村塾师的命运。两年之后,张亮基被升迁为两广总督,而左宗棠则又成为新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并跟随他六年之久。
长期共处于湖南的曾国藩和左宗棠,难免相遇,有一回,曾国藩路过左宗棠家门时,发现他正在给如夫人洗脚,便开玩笑说:“替如夫人洗脚。”这本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众人听了也都笑笑了事,但左宗棠却立刻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让曾国藩佩服左宗棠才思敏捷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些尴尬。
类似的事情并非一两次,而是随着两人的交际时有发生。在和左宗棠聊天的时候,曾国藩得知他字季高,便笑着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将“左季高”三个字巧妙地融入进去,同时也表达了左宗棠总是和自己对着干的无奈。而左宗棠听到这话并不示弱,立刻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将“曾国藩”三个字也加了进去,但语气之中竟含有鄙夷之意,令在场的其他人都不敢接话,而曾国藩本人也觉得非常难堪。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之道,曾国藩待人以诚、藏锋守拙,而左宗棠则锋芒毕露、桀骜不羁。当时的左宗棠进入仕途不过几年,所取得的成就与曾国藩无法相比,但他却丝毫不给对方留面子,并且还常常反唇相讥。周遭的人对此非常看不惯,多次在曾国藩的耳边嘀咕,认为应该给左宗棠一些教训,才能让他知道天高地厚。而曾国藩却觉得左宗棠个性如此,自己又何必和他太过计较呢。对于此事,左宗棠虽有耳闻,但丝毫不领情。
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首次带兵出战,结果在靖港大败,他气愤之下意图投水自尽,幸亏被左右拦住。回到大营之后,垂头丧气的曾国藩正好遇到左宗棠,不仅没有得到他的安慰,反而招来一顿训斥。左宗棠大骂他不该自寻短见,事情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什么要出此下策?曾国藩本就已经颓丧至极,被左宗棠这么一说更觉得无言以对。但他却还是坚持认为左宗棠只是言语直爽,并无恶意。虽然总是被左宗棠的语言尖刻所伤,但曾国藩却从未将其放在心上,坚持认为左宗棠是一个有才之人。一旦有适宜的机会,他就会大力举荐左宗棠。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上奏朝廷,为左宗棠接济军饷请功,朝廷因此任命左宗棠为兵部郎中。而左宗棠自己因为耿直的个性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受到别人诬陷,原本挪用公款的永州总兵樊燮向湖广总督状告他私役兵卒,此事被捅到了朝廷。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被传唤到武昌对质,引起了轩然大波。咸丰帝为了肃清不正之风,甚至交代湖广总督:“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都纷纷为其求情,认为左宗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后在诸多官员的担保之下,咸丰帝才放过左宗棠一次。
受到这一波折之后,左宗棠逐渐看到了官场险恶,他辞别骆秉章,颓然地回到湖北襄阳,打算从此委身江湖,远离庙堂,再也不去过忧谗畏讥的日子。而当时曾国藩正率领部队在宿松,听闻此事后便接左宗棠到自己的大营之中暂避锋芒,并时常与他探讨军情。
同年四月初一,朝廷向曾国藩特旨询问:“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接到这一旨意之后,曾国藩立刻回复朝廷:“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四月二十,清廷接到了曾国藩的奏章,随即任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曾国藩则让左宗棠回到湖南招募湘勇奔赴江西,几个月后,果然连克德兴、婺源,建立军功。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专门撰写奏折,为左宗棠请赏:“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迎头痛击,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经此奏折推举,咸丰帝对左宗棠的态度也大为改观,将其晋升为三品候补京堂。
在左宗棠四顾苍茫之时,曾国藩不计前嫌,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东山再起。虽然后世之人多喜欢谈论他二人交恶之事,但也不得不承认两人交情颇深,连左宗棠自己也曾经认为他与曾国藩是“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在三年之内,让左宗棠从一个走投无路之人一跃而成为三品大员,这种仕途传奇除了依仗左宗棠本身的才干,曾国藩的一再举荐亦功不可没。在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为其书写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4.5 不做必败之人
宦海沉浮之中涌现了很多杰出的人,成为历朝历代人们所推崇的偶像,而更多的为官之人却往往得不到一个好的下场,纵然是辉煌过一段时间却难保威名一世。这其中隐藏着的成败规律,是千年来身处宦海者孜孜以求的秘籍。那些失败的人,有些纵然是犯了大错,而有一些则是稀里糊涂就落了一个颓败的下场,从根本上来说,大多数人失败的原因大的方面是其理念与时代不合,小的方面则更多是与同僚、上司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出现问题。撇开这些外在因素不说,很多人的失败都是由于内在素养和理想的偏差造成的。曾国藩曾经说过:“昏堕任下者败,傲恨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这正是他所总结的失败之人所具备的共性。
身处于封建社会官场之中的人,所服务的对象都是皇帝,作为皇帝的耳目来协助管理百姓。一个封建皇帝并不能掌控天下所有的信息,也不能精通所有的事情,在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也自然就会出现失误,臣子的责任就是提供正确的资讯,帮助皇帝做出正确的决断。所以,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他要避免任用不贤德的人,不能任用庸才。然而皇帝或者上司的识人辨人能力总是有限的,所委派的下属贤与不贤都需要在实践之中慢慢检验,这个过程自然也就充满了风险。上司对于下属要充分信任,可一旦将信任交给了阿谀奉承之徒,便会引来灾祸。那些受到周围人所称赞的人,未必就是贤良的人;而那些不被众人所喜爱,遍受诋毁的人,也未必就是庸才。
曾国藩曾经说过:作为掌控着予夺之权的人,应该努力让自己保持辨识能力、清醒的思考能力,以及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不是将耳目完全地交付给别人。否则就只能成为“昏堕任下者”,自然也就离“败”不远了。历史上这样的人非常多,在家信之中,曾国藩便以唐玄宗李隆基的所为来告诫子弟。李隆基当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了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和张九龄等贤德之人,延续了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并创造了“开元盛世”,令唐王朝鼎盛一时。然而在他当政后期,却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昏堕任下导致天宝危机,唐王朝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切的祸端都是因为皇帝昏堕任下。
在曾国藩所认为的必败之人中,“傲狠妄为”排在第二位。他常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在曾国藩的眼中骄傲是极不可取的恶习,人因为骄傲会生出奢侈淫逸等诸多缺点,变得欲求不满,无恶不作。一个人要想自立,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必须首先去除骄傲的恶习。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弟弟:“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
一个骄傲而刚愎自用的人,势必会为自己埋下祸端。因为骄傲会使人盲目,同时失去倾听建议的能力,一味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历史上明代的朱由检正是因为刚愎自用、傲狠妄为而亡国亡家,他原本希望可以励精图治、改革旧弊,但因其个性之中的这一缺陷,误杀了很多忠良。以致国家在用人之际却人才空缺,从而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让一个身居高位者丧失本身的原则,堕入罪恶深渊,曾国藩认为多是由于“贪”字而来,他所总结的第三种必败之人便是“贪鄙无忌者”。欲望固然是人性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天性所在,但如果不能控制自己,放任这种本性肆意妄为,便会将人引上歧途。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为官者更是如此。为官者或在位者,因为自身所具备的职权,拥有了高于常人的选择权,可以让他们得到更多常人得不到的东西。这些既可以是身居高位者的特权,又可以成为引诱他们堕入深渊的诱饵,古往今来因为不能抗拒这一诱惑而落马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曾国藩对自己提出了很多要求,不贪图荣耀,更不愿意去享受那些特权,只尽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成就更为高远的功绩。对于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他也一再告诫不可越轨而为,告诉他:“福祸无门,惟人所召。”既居高位,就应立身忠正,行事廉洁,切不可贪鄙无忌,引火烧身,更不能因为获得了一些权力便为所欲为,因为那是走向失败的第一步。
曾国藩所认为必败的第四种人便是“反复多诈者”,他一向将“诚”字作为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前提,并努力要求自己首先做到。在与同僚或上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从未有丝毫隐瞒,更不会信口开河,不管做任何情况他都会首先拿出诚恳的态度获得对方的认可。而对于自己的下属,他也没有摆架子,倚势凌人,依旧以“诚”为先,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是他用人的最基本原则。在教导曾国荃时,曾国藩引用《旧唐书》中的话:“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意即和邪恶之徒断绝来往,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应该毫不迟疑,千万不要犹豫不决,不然反而会将人拖进更难脱身的泥潭;而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一定要加以重用,不仅和他们热切地结交,在任用他们的时候也要赋予完全的信任,切忌三心二意。如果可以做到这两点,那么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兴旺昌盛。而如果一个人对周围的人总是怀有诈心,任用别人也不能诚恳对待,总是疑神疑鬼,那么就会在失败的歧途上直奔灭亡。
宦海之中往往风起云涌、变幻无穷,身处旋涡之中的曾国藩不仅能够做到洁身自好,而且还能时时平安稳泰,除了因为其自身的智慧超群,更因为他善于学习总结,在古人身上汲取营养,从历史之中取得教训。他所总结的四种居官而必败之人,从反面说明了一个为官之人所应该具备的责任、道德、才干和态度,他不仅将这些认识教导给曾国荃等子弟,自己更是亲力亲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督促自己避免出现这四种错误,使自己一步步渡过风浪走向辉煌。